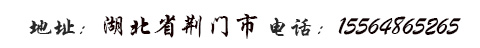电影改编的ldquo演绎rdquo
|
电影不是文学的附庸,电影语言自有它的独到魅力。深邃的电影工作者们,借鉴文本又敢于自我发挥,才使文学改编影视作品不至于食之无味。 宗城 微思客编辑,青年空间专栏作者,凤凰文化、文汇APP外约作者 张艺谋争议颇多,但很少人否认他改编文学作品的功力。《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一个都不能少》,放到今天评价都不会低。加之经由老谋子改编的作品,销量往往一下子上来,所以一段时期内,老谋子成了作家们的福音。 但老谋子的改编也有被嫌弃的时候,比如改《活着》。有的原著读者就不买账:“怎么死法都变了?结局也不一样了?”于是,他们感慨导演不忠实原著,导致电影不如小说有味道。这后半句暂且不议,但即便假设电影不如小说出彩,原因也未必是“不忠实原著”。 一些观众和读者将“忠实原著”理解为对原著细节原原本本的还原,这其实有失公允。一来,如长篇小说等文本动辄百页,细节层出不穷,一般电影长度不过百来分钟,原原本本移植细节不切实际;二来,电影和文学,体裁有异,感染受众的方式也不同。电影可以通过镜头和声音传递氛围,而文学的氛围营造寄于文本;再者,文学语言与电影语言各有侧重。文学语言擅长勾勒人物心理的“草灰蛇线”,更深入剖白人物感受。而电影语言能更简洁地呈现情感冲突、人物冲突,通过画面、声音、演员等的结合营造更直观的戏剧效果。 不遗余力地还原所谓的原著细节,最后反而可能费力不讨好,落得堆砌之嫌。小李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对原著不可谓不尊重,浮华奢靡的东部生活、特色各异的人物群像,都照顾到了。前半段尼克和黛西的对白,“Dotheymissme”、“theycouldntlivewithoutu”这般俏皮话,俨然直接挪用了菲茨杰拉德的原话。尼克和盖茨比的相见相识和最终的离别,也足见导演阅读原著的细心,但成片只是达到了“差强人意”——标准线之上,和小说比仍有明显差距。这是由于“不忠实原著”吗?可就是由于忠实原著,每一个人物都要提及,导致单个人物反而由于交代不充分,显单薄了。比如原著中的“全知视角”、故事交代者尼克,在电影里限于篇幅,很多对尼克的描述都只能一笔带过,导致这个角色略显平淡。这个缺憾,不惟小李版,早先的74年版本也有。 年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比小李版还要忠实原著,开头干脆就引用原著第一段——“在我年纪尚浅、事故不深的时候……”,要说出入,也不过盖茨比和尼克见面的场景、盖茨比与黛西约会时的天气等细节。但它的业内评价,反而还不如对原著颇有改动的年版本。00年的版本由米拉·索维诺、托比·斯蒂芬斯、保罗·路德等人出演,虽然由于经费等原因,“浮华”稍逊,但因为删除了诸多枝节,突出盖茨比和黛西这条线,使剧情更为紧凑,主要人物刻画更加丰满。 卡罗尔在《电影的力量》中如是说,“画面表现与文字表现不同,只需要简单的学习,就可以完全欣赏其中的美感。”但欣赏归欣赏,电影语言的固有特性也给意欲改编文学作品的导演们出了难题。一个问题就是对非言语行为的处理。美国教授博德威斯特尔发现,“目光、表情、姿势、身体距离等都可以被归为人物的非言语行为,在人类交际行为中占据约70%的分量”。小说能够通过大量的文字描写表现这些非言语行为,电影呢?仅仅通过对话和旁白显然不行。 聪明的影视导演,大抵就发挥他们对声音、光线、画面处理等的敏锐感。王家卫在《花样年华》中,常常安排摄像的拍摄营造出一种“层层穿越”的“窥探感”。这部电影对话并不多,却深谙留白的道理,更换的旗袍、挪动的鞋子、缭绕的烟雾甚至昏暗的路灯,都成为暗示人物心理的意象。《惊魂记》中,大导演希区柯克没有通过多余的对话营造氛围的紧张和压抑,而是在画面中展示一个水流四射的花洒,配合流水声,达到压抑、紧张的效果。这一镜头也成为了影史经典。 又比如电影《情人》中的一个情节——女主人公发现中国情人的黑色轿车停着停留于学校门口,她缓缓走过去,颇含情愫地隔窗亲吻中国情人。在这个画面中,导演阿诺刻意突出了“玻璃车窗”对两人的阻隔,营造出“这么近又那么远”的氛围。而当我们看到片尾,二人因为家境、地位、种族等原因最终分离,我们就会不由联想起玻璃车窗的暗示。他们的爱情,终归是被透明却坚硬的玻璃车窗阻隔。 世人常说老版《三国演义》忠实于原著,其实老三国并没有陷入原原本本照搬原著的窠臼,他的“忠实”,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扬弃。且不说电视剧放弃了很多涉及“神魔鬼怪”、“封建旧伦理”的情节,即便在细节上,为了渲染氛围,创作者们还在原著的基础上“无中生有”。 例如:老三国第九集,神亭岭大战后,孙策为彰显自己的爱才之心,将被太史慈撕裂的战袍挂于帐中。而当太史慈立木为信,最终带兵来投,周瑜便点破孙策高挂战袍的用心。我们看原文是如何写的: “策执慈手笑曰:“神亭相战之时,若公获我,还相害否?”慈笑曰:“未可知也。”策大笑,请入帐,邀之上坐,设宴款待。慈曰:“刘君新破,士卒离心。某欲自往收拾余众,以助明公。不识能相信否?”策起谢曰:“此诚策所愿也。今与公约:明日日中,望公来还。”慈应诺而去。诸终曰:“太史慈此去必不来矣。”策曰:“子义乃信义之士,必不背我。”众皆未信。次日,立竿于营门以候日影。恰将日中,太史慈引一千余众到寨。孙策大喜。众皆服策之知人。” 一读便知,第九集这段戏份是基于原文的“加戏”,而非一五一十的照搬。这段加戏,恰恰体现了创作者的用心。孙策将被太史慈撕裂的战袍挂于帐中,彰显这位主公的爱才;太史慈立木为信,彰显他重然诺;而周瑜的点破,更足见他和孙策关系的坦诚,以及他本人的睿智。 更为人称道的一段加戏出现在第一部的尾声,也即是原著的《曹丕乘乱纳甄氏郭嘉遗计定辽东》。曹操安定辽东,想起了逝去的郭嘉郭奉孝,感慨颇多。他立于高崖之上,面对茫茫大海,纵情朗诵《步出夏门行·观沧海》。这一段艺术加工,原著并没有,却可谓点睛之笔。 很多经典的影视改编作品,恰恰是由于导演没有墨守成规,主动求新而成。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改编自扬·马特尔于年发表的同名小说,但呈现角度颇为不同,故事结构也有调整。为了捋顺电影故事的脉络,李安还特意加了一段对上船后的人物的介绍。而像帕索里尼、库布里克这些出了名的改编好手,原原本本照搬原著从来没有出现在他们的字典里。帕索里尼的《生命三部曲》(《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一千零一夜》)、《索多玛天》,库布里克的《杀戮》、《发条橙》、《奇爱博士》、《闪灵》等电影,对原始文本都有较大程度的改编。这些作品,日后都被雕刻于电影史,甚至有的作品焕发出比原著更大的魅力。 其实,再忠实的导演们,最后也只能做到贴近原著,而所谓的“忠实”,与其说是追求情节上的高度一致,毋宁说,是通过电影语言的再创造,在荧幕上再现原著的主题、氛围、意蕴。电影不是文学的附庸,电影语言自有它的独到魅力。深邃的电影工作者们,借鉴文本又敢于自我发挥,才使文学改编影视作品不至于食之无味。 当然,也有的导演们意识到这一点,最终却交出一份让人摇头的答卷。但那不是由于他“不忠实原著”,不过是此人欠缺火候罢了。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宗城 微思客重视版权保护。本文系微思客编辑作品作品,如需转载,请事先取得授权。 联系邮箱:wethinker .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suoe.com/lldx/7766.html
- 上一篇文章: 电影怒海争锋完整版
- 下一篇文章: 南美第一海军大国,巴西订购4艘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