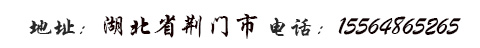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6
| 治疗皮肤白癜风 http://www.baidianfeng51.cn/第二节“我在奥普京修道院的隐居所停下,”果戈理在给A.P.托尔斯泰伯爵的信中写道,“然后从那里带走了我终生难忘的回忆。那里显然有着神的恩典,从敬拜时一些外在的特征就能感受得到。我在其他地方从没见过这样的僧侣,通过他们每一个人我似乎都可以和上帝交流。”在人生最后的几年,果戈理去过几次奥普京修道院。在寺院静谧的氛围中,他为自己饱受困扰的灵魂找到了安慰和指引。他相信这里就是他穷尽一生所追求的神圣的俄罗斯王国。在离修道院数英里以外的地方,果戈理给托尔斯泰写信说:“你可以在这里闻到寺院德行中的芬芳:一切都有治愈你的力量,人们的敬拜更加虔诚,彼此之间的友爱更加深厚。”果戈理出身于乌克兰一个虔诚的信徒家庭。他的父母在教会中都非常活跃,在家里他们也谨守所有的禁食和宗教信条。家庭中对宗教神秘主义的耳濡目染,影响了后来这位大作家的生活和艺术创作。果戈理父母的相识源于他父亲在当地教堂中神的一次启示:圣母玛利亚出现在他面前,用手指着他身边的一个女孩对他说,她将成为你的妻子,而后来事情真的就是如此。和他的父母一样,果戈理并不满足于仅仅遵守教会的教条。从很小的时候他就期待着能够亲身经历神灵现身,以满足他内心深处的渴求。年他给母亲写信说:(在我小时候)我看待每一件事都是通过别人的眼睛;我去教堂要么是因为被要求去,要么就是被人带去;但是我一到那就只能看见十字褡、神父和大声咆哮的执事。我在胸前画十字是因为我看到别人也都这样做。但有一次——我现在依然能够回忆起当时的每一个细节——我让你给我讲讲审判日的故事,你讲述得如此生动如此全面,等待着那些义人的美好事物是如此动人,而等待着那些罪人的永世折磨在你口中显得如此恐怖,使我的身心都感受到震撼。这次经历让我日后中心有了崇高的思想。跟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果戈理从来没有对宗教产生怀疑。他晚年心灵上的煎熬也是因为怀疑自己在上帝面前是否能称得上义人。但作家坚定的信仰并不从属于任何教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就像他自己也承认的,他的信仰和新教徒十分接近,他更相信个人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不过从年到年,果戈理在罗马生活期间,他与天主教传统的关系也十分亲密。之所以没有选择皈依罗马教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他看来两种宗教之间没有什么明显差别:“我们的信仰和天主教是一回事,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从一个转向另外一个。”在他从未发表的《死魂灵》的最终版本中,果戈理原本设想其中的神父一角兼具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优点。他似乎一直在寻找一个能够将所有人以基督徒之间的友爱联结在一起的精神教会。在奥普京修道院,他认为自己找到了这一理想的“俄罗斯灵魂”。果戈理的小说是他精神探索的舞台。和许多学者的观点相反,果戈理其实并不存在所谓早期“文学作品”和晚年“宗教作品”之间的割裂,尽管他后期对宗教表现出更明显的兴趣。果戈理所有的创作都有着神学上的重要意义——它们确实开辟了一个赋予小说和宗教启示同等地位的民族传统。他的许多故事都应该当作宗教寓言来读。那些古怪奇特的人物并不有意再现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圣像,给世人以启示。这些人物让人思考另外一个世界,那里善与恶正在展开一场争夺人类灵魂的战争。在果戈理早期的作品中,这种宗教象征大多寄托在圣经式的主题或非常隐晦的宗教隐喻当中。例如《外套》就呼应了圣亚加索(St.Acacius)的生活——他是一名隐士(和裁缝),在受到长老多年的虐待之后死去,后来这位长老忏悔了自己的罪过。这解释了《外套》中主人公为什么叫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他是圣彼得堡一名卑微的公务员,被人抢去了一件珍贵的外套,最后凄惨死去,死后成为幽灵到城里复仇。在《钦差大臣》()失败之后——作者创作这部戏剧的本意是要作为一篇道德寓言,但大众却把它当作讽刺喜剧——果戈理决定在创作中让自己传达的宗教信息更容易理解。此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一部三段式小说《死魂灵》的创作中。这是一部但丁《神曲》般的史诗,俄罗斯的天命在最后得以揭示。俄国乡村的各种缺点在小说最终仅完成的第一章()中被暴露出来,而在未完成的第二、第三章中,作者本想通过描写崇高的、“真实存在的俄罗斯灵魂”来否认这些缺点。主人公乞乞科夫在农村骗取濒死的乡绅和他们死去的农奴(或“魂灵”)的身份,从政府获得大量钱财。但即使这样一个恶棍,随着果戈理创作主题转向基督的爱和手足情谊这种斯拉夫式理想,乞乞科夫最后也被上帝拯救,成了一个地主。这部“史诗”的整个概念就是俄罗斯的“再生”,以及它精神上在“人类通往完美的无尽阶梯上”不断地向上攀登——这也是他从《圣经·创世记》中借鉴的雅各布天梯的故事。果戈理关于神圣异象的灵感来自他所拥护的斯拉夫派人士,他们梦想着俄国能够成为纯洁基督徒的神圣联合之地。果戈理对缺乏灵魂、个人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满怀担忧,斯拉夫派的思想对他而言自然充满吸引力。其根源是俄国教会作为一个充满友爱的自由基督徒团体,正如神学家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在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所勾画的概念——一种“自由的统一体”(sobornost,来自俄语sobor,指代“大教堂”和“集会”)。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这个概念来自一套神秘主义理论。他说,信仰不能通过理性获得,必须通过亲身体验,从内心深处感受基督的真理,而不是靠教条和律法。真正的教会不能规劝或者强迫人们成为信徒,因为除了基督的爱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个权力。作为一个自由选民的群体,它只存在于基督爱的精神之中,正是这种爱将虔诚的人和教会联系在一起,也只有这种精神是他们虔诚的保证。斯拉夫派相信真正的教会是俄罗斯式的。跟西方通过律法和僵化的等级制度(例如设置教皇)来行使自己权威的教会不同,他们认为,俄国的东正教是真正的精神共同体,而基督是他们唯一的领导。毫无疑问,斯拉夫派对俄国教会抱有批判态度,认为他们和沙皇政府间过于亲密的关系已经削弱其精神属性。斯拉夫派支持一个社会性的教会,有些人或许会称之为社会主义者的教会,这使得他们很多关于信仰的文章都被政府查禁(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的神学作品直到年之后才得以出版)。斯拉夫派是农奴解放运动的坚定信徒:因为只有精神和身体完全自由的个人才能组成俄罗斯式的真正教会。他们相信俄罗斯人民拥有基督徒的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真正的教会。斯拉夫派相信只有俄罗斯人民才是世界上真正的基督徒,他们农村公社的集体生活(一种“基督徒真爱与友爱的结合”),他们温和谦逊的品质,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为了更高的道德追求牺牲个人自尊的意愿,而这种更高的追求就是公社、国家和沙皇。凭借这些基督徒的品质,俄罗斯已远远不止是一个民族——他们身上扛着对世界的神圣任务。用阿列克谢的话来说:“俄罗斯人民已不仅仅是人民,而是全人类。”这就是关于“俄罗斯灵魂”的构想,果戈理打算在《死魂灵》的第二、第三部分来描述它,人们认为它是将要拯救基督教世界的普世精神。民族之魂或民族精髓的概念在浪漫主义时期十分常见,但果戈理是第一个给“俄罗斯灵魂”赋予了救世含义的人。这一概念源自德国,在那里像弗里德里希·谢林这样的浪漫主义者创造了民族精神的概念,用以将本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区分开来。19世纪20年代,谢林在俄国享有神一般的地位,他关于精神的概念被那些想要将俄国与欧洲区分开的知识分子奉为圭臬。作为谢林在俄国的头号门徒,奥多耶夫斯基公爵声称,西方人为了追求物质进步,已经将灵魂卖给了魔鬼。“你的灵魂已经变成一台蒸汽机,”他在小说《俄罗斯之夜》()中写道,“在你身上我看到的是螺丝钉和齿轮,而看不到生命。”现在只有俄国和她年轻的灵魂可以拯救欧洲。这印证了一个规律,就是像德国和俄国这样在工业化进程中落后于西方的国家,更容易产生民族之魂这样的概念。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缺失,可以通过其保持原生态乡村中的精神美德找回一点平衡。民族主义者认为淳朴的农民身上具有创造性的自发性和友爱精神,而这些品质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早已经消失不见。在18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间,俄罗斯灵魂的概念在这种模糊的浪漫主义思想中开始发展起来。彼得·普拉维利希科夫的论文《论俄罗斯灵魂的内在特质》()提出了一些观点,例如俄国有一种自然的创造力,要比西方的科学有更大的潜力。这位剧作家被这种民族自豪感冲昏了头,甚至断言俄国有许多看似不可能的第一:我们以为农民发现了连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名医)和加仑(希腊解剖专家、内科医生和作家)都没有发现的药酊。阿雷克西沃村子里的正骨医生在外科手术的领军人物中十分出名。库利宾和来自特维尔地区的机械师索巴金在机械技术方面都技艺高超……俄国人无法发现的东西,对于全人类来说将是永远的未知。在年胜利之后,关于农民灵魂的概念以及他们无私的美德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开始与俄罗斯将是西方的救世主的说法联系起来。这是果戈理最初在《死魂灵》中所担负的使命。在更早的《塔拉斯·布尔巴》中,果戈理将俄罗斯灵魂归因于一种只有俄国人才能感受到的爱。“没有哪种感情比这样的同志情谊更加神圣的了!”主人公塔拉斯·布尔巴对他的哥萨克族人说:父亲爱自己的孩子,母亲也爱自己的孩子,孩子则爱着自己的父母。但兄弟们,这并不完全相同,就连野兽也爱自己的孩子。然而精神上而不是血缘上的紧密联系,是只有人类才有的。别的国家也有志同道合的同志,但和俄国土地上的友爱相比就不算什么了……兄弟们,俄罗斯灵魂的热爱,并不是只用头脑或者你身体的某一部分,而是用上帝所赐予你的一切去爱。果戈理与斯拉夫主义者靠得越近,越相信这种基督徒间的友爱是俄国带给世界的独特启示。在《死魂灵》第一章最后令人难忘的三驾马车(troika)一段中,果戈理曾透露过关于“俄罗斯灵魂”天启般的图景:俄罗斯,你不也像这快得谁也赶不上的三驾马车一样奔驰吗?只见大路在你轮下扬起尘土,桥梁被你震得隆隆作响,一切都被你超越而落在后面。过路行人被这种神奇的景象所惊骇,停下脚步问道:这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闪电?这令人震战的狂奔意味着什么?喂,骏马呀,骏马,你们有多么了不起!你们的马鬃里是不是带有旋风?你们的每根血管里是不是带有敏锐的耳朵?一听到天上传来熟悉的歌声便一齐挺起红铜板的胸膛,几乎蹄不沾地在半空中飞驰,身子变成一条线,只有得到神的鼓舞你们才会跑得这么快!俄罗斯,你要奔向何方?请给个回答。你不肯回答,只是铃儿发出美妙的声响;空气被风撕成碎片,呼啸不停;大地上的一切从旁边掠过,所有其他民族和国家都侧目而视,退到一旁,为她让路。基督徒之爱的“俄罗斯准则”——果戈理将在第二、第三部分揭示——旨在将人类从西方世界自私的个人主义中拯救出来。正如赫尔岑在读完果戈理这部小说之后评论的那样,“俄罗斯的灵魂中隐藏着巨大的潜力”。果戈理在这部小说上花的精力越多,越觉得揭示“俄罗斯灵魂”中的神圣真理是自己肩上所背负的使命。“上帝只赐给我完成并发表第二部分的力量,”他在年给诗人尼古拉·亚齐科夫的信中写道,“然后他们会发现我们俄国人身上有很多他们猜都猜不到的东西,而这些我们自己并不愿承认。”果戈理想从寺院中寻求神的启示——他相信俄罗斯的灵魂就藏在这里等待被发现。他最敬佩奥普京修道院中隐士的一点就是,他们对于掌控自身欲望以及洗涮自己灵魂罪过的能力。他认为这种自律精神就是解决俄罗斯精神顽疾的良方。这次又是斯拉夫主义者将果戈理带到了奥普京修道院。基列耶夫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曾多次去那里拜访玛喀里神父,两个人整理了派西神父的生平,并将早期教父的作品由希腊语翻译过来。和他之后所有斯拉夫主义者一样,基列耶夫斯基相信奥普京修道院的隐士是东正教古老精神传统的真正象征,这里是“俄罗斯灵魂”最活跃的地方,当果戈理从国外回到莫斯科,那时出入沙龙的全是奥普京修道院的信徒。《死魂灵》被当作一部有宗教指导意义的作品。它的写作风格带有强烈的以赛亚精神特质——以赛亚在《圣经》里预言了巴比伦王国的覆灭(在创作《死魂灵》第二部分的时候,果戈理在他的信件中经常引用这一景象)。果戈理在绞尽脑汁创作这部小说时,也沉浸在自我预言的宗教狂热之中。他埋头研究7世纪西奈半岛神学家约翰·克利马科斯的著作,后者主要论述一个人灵魂纯净以及攀登通往完美精神世界的阶梯(果戈理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使用了这一场景,他说自己还在阶梯的最底端)的必要性。果戈理唯一的安慰来自不停地祷告,他相信从中可以获取完成创作《死魂灵》这一神圣任务的精神力量。“为我祈祷吧,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他在年给奥普京修道院的菲拉雷特神父的信中写道:请尊敬的修道院院长,请主里所有的弟兄姐妹,请那些最虔诚也最热衷祷告的信徒,请他们为我代祷。我所选的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没有上帝每天每时每刻的帮助,我的任务不可能完成,我的笔动都动不了……慈爱的上帝,他有成就一切的权柄,能把我这样像煤炭一样黑的作家,变成一个纯洁无瑕只开口谈论圣洁与美妙事物的人。问题是果戈理没有办法描绘出这样一个圣洁的俄国,这样一个满是基督徒情谊的王国——而他将这视为自己的天授使命。所有俄国作家,即使那些最有想象力的,也无法描绘出这样一个地方——或者说,没有一处能满足作家吹毛求疵的要求。无论他如何努力去赋予笔下的俄国主人公理想的形象——一幅俄罗斯灵魂的圣像,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果戈理对现实的观察,让他总是忍不住将人物原型身上奇奇怪怪的特点嫁接到他们的形象之上。当他对自己打上宗教光辉的做法感到绝望的时候,他写道:“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只要一个人转而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suoe.com/lldx/9707.html
- 上一篇文章: 专栏梁利锋20赛季英超前瞻
- 下一篇文章: 图画展览会名家名团力献穆索尔斯基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