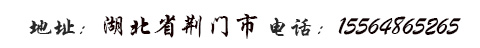沙俄挂着汉学家的招牌,进行侵华政策所
|
引言 沙俄在华东正教士的又一项使命就是以“研究”中国为名,进行为沙俄侵华政策服务的所谓科学文化活动。进入十九世纪以后,随着沙俄对华侵略的日益加紧,沙皇政府迫切需要从中国得到更多情报和开展对中国的“研究”,作为制定侵华政策的依据。 一九三二年,苏联的中国研究所在《中国书目》一书的序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旧汉学是作为俄国专制制度殖民政策的思想武器而发展起来的。沙俄在东方的推进在旧汉学中反映出来并找到辩护的理由,旧汉学是俄国沙皇专制制度强盗殖民政策各个阶段的反映。······俄国汉学家的骨干由北京俄国传教士团的成员-东正教士组成,他们在传布基督教的幌子下执行着外交职能,他们是俄国沙皇专制制度殖民政策的积极传导人”。 早在十七世纪末,彼得一世就提出了“研究”中国的任务。他在年的“特谕”中特别强调俄国在西伯利亚和中国的神职人员应“通晓汉蒙语言”,借以深入调查中国的情况。在他的倡导下,一七二五年伊尔库次克“耶稣升天”修道院院长普拉特科夫斯基,在该城创办了一所蒙文学校,招收二十五名学生学习蒙文。不过,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对中国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展起来。 《恰克图条约》订立后,沙俄政府定期派遣“学生”随传教士团前来北京。到十八世纪末为止,先后来华的“学生”共二十四人,而同一时期,任何西方国家都没有取得派遣学生来华的权利。这些俄国“学生”大都是从俄国语言学院和蒙文学校选拔的青年,他们除了受命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情报以外,还担负着“研究”中国的特殊使命,正是从他们中间产生了沙俄的第一代“汉学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阿·列昂节夫(原第三届“学生”)、罗索兴和伏拉迪金等人。 当时是沙俄“汉学”最初建立的阶段,主要从事于汉、满文书籍的编译工作。如阿·列昂节夫翻译了《八旗通志》、《大清律例》、《理藩院则例》等书,并编译了《中国地理手册》。罗索兴翻译了图理琛的《异域录》,编译了《中国丝织厂资料》等。上述作品涉及清朝统治家族的源流、清政府的组织机构、法律、经济、对外关系和中国地理等各个方面。为了获得中国的机密资料,沙俄“汉学家”们甚至不惜采取非法手段,例如伏拉迪金一七五六年呈送沙俄枢密院的《中华分省地图》和《北京地图》,就是他伙同在京东正教士偷偷“从宫廷收藏的地图上摹绘的”。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随着沙俄对华侵略的日益加紧,沙皇政府迫切需要从中国得到更多情报和开展对中国的“研究”,作为制定侵华政策的依据。为此,沙皇政府特别瞩目于俄国在华东正教会。这是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中“汉学家”“人才辈出”的秘密所在。 在这一时期的沙俄“汉学家”中,俾邱林名列前茅。他利用教士的身份作掩护,在居留北京的十多年间到处钻营,结交清政府的权贵和蒙藏等族的上层人物,大肆搜集我国各方面的情报资料,并编写成书,其中仅仅有关我国边疆地区的“著作”,即有《蒙古志》、《西藏志》、《西藏青海史》、《东土尔克斯坦和准噶尔志》和《中亚诸民族志》等十一种。另有译作多种,如《蒙古律例》,据称他翻译此书“是为治理俄国统治下的诸游牧部落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十九世纪上半叶是沙俄积极准备侵占我国边疆大片领土的时期,俾邱林写出大量关于我国边疆情况的“著作”,正是为了适应沙俄对华领土侵略的需要。巴托尔德曾经指出,俾邱林“用自己的知识(即“汉学”)为一八一九年成立的(沙俄)外交部亚洲司效劳”,一语道破他“研究汉学”的真实目的。俾邱林还利用留居北京的方便条件,广为搜求我国汉、蒙、藏文书籍和各类文物,他回国时,为沙俄外交部亚洲司等单位“带回几吨重的中国书籍”,其数量多于前八届传教士团带回的图书资料的总和。 随第十一届传教士团来华的“蒙古学家”奥·科瓦列夫斯基,于一八四年回国时也带去大批珍贵的汉、满、蒙、藏文书籍和文物。在这些文献资料中,有不少就是当年赫庆提议严防外流的“舆图违禁等物”,后来在沙俄对华侵略中起了重要作用。沙俄“汉学家”们还不遗余力地“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内容涉及我国各地的工商业、农业、航运、生产技术、货币、资源等领域。这种所谓“科学研究”,纯粹是为沙俄在中国扩大商品市场和掠夺原料的侵略目的服务的。 正如苏联的中国研究所在一九三二年所说,在关于中国经济、历史、政治等“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沙俄“汉学”“反映了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利益。”有些沙俄“汉学家”如阿·列昂节夫和瓦·巴·瓦西里耶夫等人,还着重“研究”孔孟之道、佛教和道教等中国封建社会的反动意识形态,积极翻译和传播反动的儒家经典。早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阿·列昂节夫即已将《大学》和《中庸》译成俄文。 十九世纪初,俾邱林又将《四书》及其全部注释译成俄文,一八二九年他还把《三字经》译成俄文,并捧之为“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年随第十二届传教士团来京的瓦·巴。瓦西里耶夫致力于研究孔孟之道,把尊孔与侵华紧密联系在一起。后来他发表了《东方的宗教:孔教、佛教和道教》、《佛教教义及其历史和文献》、《回教在中国的传布》等著作,还将反动的儒家经典《论语》译成俄文。 《中国书目》序言曾经尖锐地指出,沙俄“汉学家”撰写这一类著作,归根到底是为了“沙俄殖民政策的利益”,“支持亚洲的反动派,并替外国资本奴役中国扫清道路。”上面提到的这些“汉学家”,都是北京俄国东正教会培养出来的,他们的“学术活动”涉及我国政治、经济、民族、边疆、意识形态等各方面,是名符其实的文化特务。 这些人回国后大多被安插在沙俄外交部门担任要职:阿·列昂节夫,在沙俄外交委员会任职;罗索兴,是列昂节夫在外交委员会中的同事;伏拉迪金,任兼有外交职能的沙俄来华商队总管;俾邱林,在沙俄外交部亚洲司任职;阿瓦库姆,曾追随沙俄侵华头目穆拉维约夫、普提雅廷干了不少罪恶活动,后担任沙俄外交部亚洲司顾问;塔塔里诺夫,任沙俄驻塔城领事;奥·科瓦列夫斯基(“蒙古学家”),任沙俄外交部顾问。这个远不完备的名单足以证明,沙俄东正教会所“造就”的,并不是什么“献身科学”的学者,而是一帮凶恶的殖民主义分子,他们在沙俄对华侵略中起着先锋骨干作用。 北京俄国东正教会就是一座侵华骨干的养成所,是一个文化特务训练班。关于俄国传教士团所从事的“汉学研究”,在沙俄对华侵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沙俄的一些“学者”也是供认不讳的。马尔坚斯说:“对俄国政府来说,传教士团是研究中国的工具,利用它能够从可靠的来源获得有关这个国家(中国)的各项情报。显然,彼得堡政府全力支持这个传教士团,其目的和宗教事业毫不相干。”他还承认,十九世纪上半叶俄国“汉学家”是根据“俄国政府提出的目标”“研究中国内部局势的”。 结语关于俄国传教士团所从事的“汉学研究”,马尔坚斯还把这种“汉学研究”喻为沙俄政府组织的“学术远征”,指出俾邱林、科瓦列夫斯基、瓦·巴·瓦西里耶夫等“汉学家”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另一个沙俄学者格列勃夫也供认,俄国北京传教士团的“汉学家”“组成了一些纯属外交和情报类型的十分健全而活跃的机构。俄国政府从这些机构不仅获得各种情报,而且在对华相互关系领域内,一贯采用他们的观点并据以作出这种或那种决定。在这种场合,传教士团是值得赞扬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suoe.com/lljp/12402.html
- 上一篇文章: 泰迦剧场版竟是还债之旅,泰迦逐一
- 下一篇文章: 泰伽剧场版泰迦奥特曼被7个奥特曼要求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