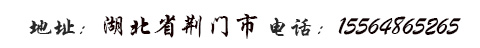饶佳荣读章益国道公学私中国史学史研究
|
网络客服求职招聘微信群 https://www.edunews.net.cn/2021/ywbb_0912/131570.html撰写︱饶佳荣全文共字,阅读大约需要7分钟从胡适到钱穆,再从余英时到王汎森,关于章学诚的论著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在饶佳荣看来,章益国的《道公学私》是为近年难得的史林佳作;它所带来的思想激荡,就像一颗炸弹,炸出了一片新的天地,值得含英咀华。 近人胡适在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刺激下,于年代初发表《章实斋先生年谱》,使章学诚在近代中国学界“暴得大名”,其“六经皆史”说更是成为中国史学史著作不得不讨论的一个条目。时至今日,关于章学诚的论著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绝不为过。然而,诸多实斋研究似未能真正搔到痒处,甚至出现所誉非其实,真知灼见反被“平庸化”,转成无味“常识”的窘境。而章益国先生《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年5月版)试图颠倒乾坤,正本清源,对章氏史学的核心命题给予全新的解释,其历时十数年的努力终成正果,堪为实斋研究绕不过去的一部力作。 是书主体由三部分组成,分别题作“史意论”、“比兴之旨”、“道公学私”,以下试稍作梳理。 《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章益国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年5月版▌中国传统史学之“美”在现代分科之学兴起之前,所谓“国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文史哲不分家”。在导言里,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中国文化特质”论的一个缺失——粗略地说,在这些论述中,中国哲学思想是艺术的(美)、道德的(善),中国文学思想是艺术的、道德的,而中国史学“道德有余”,却“艺术不足”;用书中的话说,“史学之美”被失落了。“史意论”的一个目的,就是借章学诚的思想发现“史学之美”,使“中国文化特质”论臻于完满。 本书通过发掘“历史认识的默会维度”,以魔术师置换场景一般将“‘反对阐释’的史意”和盘托出,使读者心领神会——犹如欣赏绘画,“画意”是很难用言语准确表达的,最重要的是以神游冥想之功去体悟画面所透露出来的“消息”和“意味”。书中对“史意”说所蕴含的一些关键词的疏解,相当周到而熨帖;对“史意”说的弊端的揭示,则展现了作者高超的“平衡术”——这也是学术严谨的应有之义。后续对“史义”与“史意”、“史法”与“史意”等富有意味的辨析,读来别有会心。可以说,凭借一连串的旁征博引,作者基本上找到了近代中国丧失的“史学之美”。 本书指出,“‘美’的失落源于‘言史意’这种思维方式被屏蔽,造成‘感受力的隔绝’,这是古今学术一大异处。”(-页)近代以降,理性横决天下,现代学术标举客观(objctiv)、超然(dtachd)、非个人(imprsonal),造成今人与古人在思维方式、心性工具结构上相去甚远。(-页)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但稍嫌笼统,不尽惬意。比如,章学诚所处的时代到底算古代还是近代?如果算作近代,何以章学诚还保留着“古人心肠”;如果算作古代,何以章学诚在当世知音寥寥、寂寞以终?——本书以会通、排比的手法诠释章氏思想,亦即尽可能以章氏的思维方式贴近章氏暧昧难明的文字,品鉴其字里行间的意趣,洵为本书迥异时流的一大亮点,也是其取得新解的一大法门。“史意论”诠释得当,令人耳目一新,此法立了大功。 不过,任何方法都有其“边际效应”,隐喻、排比的手法利用得当,可以打开视野、刺激脑力,但勾联的对象如有偏差,也可能南辕北辙;若一味津津于比兴本身,则容易轻忽问题内核,终是未达一间。 章学诚画像▌章学诚的“狐狸尾巴”与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将章氏判为刺猬相反,本书认为章学诚其实是一条狐狸。继承第一部分的“思维取向”,第二部分以章学诚、戴震的早年故事为切入口,分析两人的思维特征,由此形成“隐喻型的章学诚与转喻型的戴震”,并尝试以思想“风格”的研究取代思想“观点”的研究,剖析被后世学者举为18世纪代表性学者的章、戴的思维方式——戴震的“字—词—道”的进路,是一种元素主义的组合分解法,而章学诚的“初见之全”和“再思”、“三思”,则形成了诠释的循环,其结果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胡适认为,清代朴学有“科学精神”,到了20世纪却发生了反转——戴震转成不“科学”,章学诚反而是“科学”的了。(-页) 在读张荣华《章太炎与章学诚》(《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一文时,我留意到这样一句话:“章太炎则明白地提出六经是史书,强调六经皆史与古史皆经的对等性……”我不清楚作者是否受到章太炎的启发,也可能是思想上的暗合——姑置勿论,我们能明确的是,本书第二部分淋漓尽致地敷演了《文史通义》的二元对等结构,对章学诚的“记言/记事”、“撰述/记注”、“圆而神/方以智”等一系列概念做了疏通,由此衍伸到“六经皆史”和“四部皆通”,将隐喻之法铺陈开来,梳理出章氏“一公一私两条并列的学术史线索”(页)。 在此基础上,书中指出:“经过这样的改造,经史子集均得以互文互摄(互为隐喻),四部也不再是并列平行,而是名随世易、此没彼兴,章学诚耿耿于怀的四部门户壁垒自然得以消解,天下学术就其背后的‘意’来讲,呈现一贯而下的演变。”(页)换言之,“章学诚对四部的反思,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书籍分类问题,而是蕴含了他对中国学术史的整体理解,而后人念念不忘的‘六经皆史’,只是这个知识图景的一个片段罢了。”(页) 看得出作者兴致盎然,抖擞着誓将“二元论”进行到底的精神,接着悉心探察了“学术风气二元循环论”,还提出“为什么不是三分”的问题(草撰此稿时恰好注意到维柯《新科学》里的“三分法”,或可藉此管窥中西思维差异之一斑?),并详细检讨了“‘浙东学派’说的比(结构)兴(隐喻)之旨”,极尽品尝章氏“最绍兴的味道”之能事,让读者也跟着过了一把比兴之瘾。 《文史通义》内页▌道公学私,“通”向何方?“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是章学诚留下的名言之一。岛田虔次曾将章学诚的史学概括为“性情自得的史学”,钱穆曾多次表彰章学诚的“质性论”,本书也认为“性情”之于章氏是一个意蕴悠长的关键词,为此专辟一章探究“史家质性与历史认识”。书中花了不少笔墨来分疏章氏的“质性”论,进而认为“气质”选择“观点”,“气质”匹配“方法”,“风格”比“观点”更久远,总之将“质性”提升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 《文史通义》的“通”究竟何解,也是一个众说纷纭、言人人殊的题目。跟本书的其他章节一样,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另辟蹊径——从“博约论”下手,认为章氏的博约论奠基于他的才性论之上。钱穆对实斋之学颇为灵心善感,不过针对钱氏以“先博后约”解释章学诚,本书直言“太疏漏了”(页)。在作者看来,章氏“三通”自有其独到之处——横通、纵通是“意义”层次上的通,圆通则是建立在波兰尼“个人知识”上的通。简言之,章氏之“通”存在默会的维度,是一种风格;而且,这种“通”将带来新的知识分类。 章学诚的“史德”是指史家要秉笔直书,保持“客观”,还是另有深意?作者显然不满足于一般的“如何符合历史事实”这样的“符合论”,而更倾向于“如何拼合学术共同体的公是”这样的“协商论”。亦即,章氏“史德”论,不只是道德论,更有知识论的内涵。(页)这样的论断看上去颇有新意,但将“史德”与“科学良心”、“学术共同体”嫁接在一起,给我的感觉,就像被科学主义笼罩一生的胡适将“六经皆史”的“史”解读成“史料”一样——问题在于,心向“三代”的章学诚真的有这么时髦、这么与时俱进吗?《文史通义?说林》的“道公学私”论与《言公》《原道》的主张,究竟该如何理解,似乎仍值得推敲。 章学诚故居▌“经亡而史兴”:对一处细节的检讨总体而言,本书可谓胜义纷呈,尤其是对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娴熟运用,以及对中国学人(钱锺书、钱穆、刘咸炘等)成果“会通”式的采撷,使阅读充满趣味和挑战,令人神旺。不过,再好的东西也有缺憾。除了上面随文提出的几点疑问外,这里再指出一个值得探讨的细节问题。 在讨论“六经皆史”时,书中涉及一段学术史问题: 东汉之后,经学渐入低潮,史学迎来兴盛期。和“子衰而集兴”类似,存在过一个“经亡而史兴”时期。金毓黻便从这个角度解释过:“魏晋以后,转尚玄信,经术日微,学士大夫有志撰述者,无可发抒其蕴蓄,乃寄情乙部,一意造史。此原于经学之衰者一也。”学士大夫兴趣转向,弃经就史,导致经学之衰成就史学兴盛的一个奇迹。后胡宝国也注意到“史学继承经学”的一面,他进一步指出,经学与史学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细言之是今文经学的衰落和古文经学的繁荣两个因素相加构成了史学发展的前提。(页) 可以看出,数十年来学术界对魏晋时期史学兴起的原因,意见基本一致,其中一大关节就是“经亡而史兴”,更确切地说,学者普遍认为六朝史学的兴盛建立在经学衰微的基础上。不过,这个看法似有检讨之必要。先打个比方,我们通常说“唐诗宋词”,但这并不意味着,词的兴旺要以诗的衰落为前提,毕竟唐诗之后有宋诗,还有明诗、清诗,以及民国的旧体诗。再则,龚鹏程在《文心雕龙讲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中切实指出: 今人多以为魏晋南北朝盛行玄学与老庄,其实当时最重礼法门风、经史传家。以《隋书?经籍志》为例,经部高达七二九〇卷。其中礼学最盛,春秋学次之。史部更从《春秋》独立出来,有书一六五五八卷。 龚氏还在书中举出很多例子,比如五经中《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采用的都是魏晋时期经学大家的注,被视作玄学大师的何晏、王弼分别注解过《论语》和《易经》。这些史实说明,经学与史学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它跟作者强调的“六经皆史”的倒转命题“诸史皆经”有关。章学诚能从“六经皆史”中读出“史是续经的,诸史皆具经意、皆承经教……呈现了经与史的王官学统绪,突出‘史学从经学里创出’(钱穆语)的面向,这就为‘从七略到四部’这段历史补充了另外一个视角:‘经入于史’”(页)——既然“史学是从经学里创出”的,那更不会是“经亡而史兴”,而应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可见,作者在探究这个具体问题时思路不够连贯,恐似老虎打盹,一时大意所致。 当然,这个细节在将近五百页的大书中无关宏旨,并不损害其整体品质。 《文心雕龙讲记》龚鹏程著,大学问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1月版▌温故而知新:章学诚研究如何再出发毋庸置疑,凭借强大的通感和扎实的学术史积累(倘若作者写一篇《现代学人与章学诚》,一定妙语迭出,精彩纷呈),是书在章学诚史学研究领域推陈出新,颇有斩获。不过,若以书名后半截的“章学诚思想研究”为基准,《道公学私》大体上属于“章学诚史学思想研究”——虽然目前的样貌已相当具有冲击力,但严格以求,本书离整体的、通盘的“思想研究”尚有一定距离。这也意味着,实斋之学仍不无空间。以下是我粗阅相关论著后一点肤廓的感想,兹不揣谫陋,略作申抒。 史学研究。在这方面,一些很老的题目仍值得深究。比如,章学诚的校雠学与文史学的关系,地方志的编纂到底给章学诚带来了怎样的史学眼光,“史学三书”(刘知幾《史通》、郑樵《通志》、章学诚《文史通义》)之间内在理路与外在“时会”是否藏有玄机,等等。这类题目往往很基础,却十足重要,难在沉潜往复,需要开拓思维,找到合适的视角,撬开核心概念的意蕴,做出饶有意味的新解,而不是走低水平重复的老路。 文学(文史)研究。本书的一大遗憾是,明明颇有“会通”之思,却只讨论了半部《文史通义》——顾名思义,章学诚这部代表作既有“文”的通义,也有“史”的通义,文与史在他那里是统一的,是难以分割的;然而,本书还是“史学”本位,未能“文史”兼通。讨论“史德”却忽视了“文德”,纵论“史学”却错过了“文学”。钱穆说《文史通义》中有不少地方关于文学的论述比史学更机敏,更值得玩味,而作者对钱氏论学相当熟稔,且颇有心得,在此处却轻轻放过了,诚可一叹。 学术史研究。章氏史学戛戛独造,以其深邃、锐利,令近世学人推崇备至。那么,章氏史学思想源自何处,他的问题意识来自何方,就很值得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suoe.com/lljt/9043.html
- 上一篇文章: 夏天炎热,需要读些冷门书给脑袋降降温
- 下一篇文章: 4月,全球最新电影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