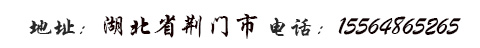罗索阅读了黑暗之心之后决定,尽快阅读
| 福建白癜风微信交流群 http://www.cgia.cn/news/chanye/1662152.html年之后,康拉德作品在情感层面上变得不那么强烈,更多地转向“外部”因素。根据康拉德的传记作者弗雷德里克·卡尔的说法,“《在西方的目光下》的问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某种意义上,对康拉德来说是,—那一段时间是一个分水岭,这在心理上突出表现为他持续4个月的精神崩溃,实际上以结束整个具有个人特点的创作活动的方式显示出来。完成《在西方的目光下》之后,他将回到《机缘》,回到篇幅较短、较为轻松的小说,回到《胜利》。与—年的小说相比,在这类作品中,他的个人特征大大减少。根据卡尔的观点,在《在西方的目光下》中,康拉德触及了每个艺术家必须或者试图实现的事情:深入挖掘自己的心灵,去发现自己最恐惧的东西。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他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接着,卡尔发现,康拉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方面具有有趣的相似性,两人都进行了强度很大的自我探索。但是,在罗素看来,康拉德在这一点上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截然不同:两位作家都致力于发掘人的心灵的隐蔽部分,发掘人羞于启齿、深感担心的冲动和欲望,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看来是说明了实现神灵救赎的需要,康拉德创造的角色却说明了自我控制的必要性和价值。正如罗素所说,“他康拉德强烈地意识到,通常出现的强烈的精神失常具有各种形式,正是这种状态让他对约束的重要性形成了深刻见解”:有人也许会说,他的观点与卢梭的看法相反——“人出生在枷锁中,然而可以变得自由。”所以我觉得,康拉德会说,他变得自由了,其方式不是放纵自己的冲动,不是采取漫不经心和不加控制的态度,而是让难捉摸的冲动服从占主导地位的目的。罗素说,从根本上看,现代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哲学:一种源于卢梭,鼓吹放弃所有形式的约束;另一种寻求从人的外部强加约束。这两种哲学都应加以排斥:康拉德坚守更古老的传统,认为约束应该来自人的内心。他一方面鄙视没有约束的做法,另一方面讨厌仅仅来自外部的约束。在所有这些方面,我发现自己与他十分一致。在他寓言性的短篇小说《秘密分享者》中,康拉德在这方面的态度也许得到了最佳说明。在这个故事中,一位年轻的船长惊讶地发现,他的船上有一名逃犯——一名从另外一艘船上逃出来的杀人犯。在平常情况下,船长的职责是,把这个人交出去。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把逃亡者隐藏在自己的舱房里,既不让他自己的船员知道,也不让正在寻找那个人的船长知道。他冒此危险的原因是,他对逃犯持强烈的认同感,两人几乎在刚刚见面之时,便形成了一种“神秘的交流”。这位船长说:“我仿佛在一面巨大的灰暗的镜子的深处,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他意识到,他自己很可能处于这个杀人犯的境况之中;如果他遇到相同的情形,他也可能动手杀人。在小说中,那位船长反复想到,自己与逃犯的身份相同,将自己舱室的这个“秘密分享者”视为他的“另一个自我”,“秘密自我”或者“第二自我”——实际上,康拉德曾考虑将这三个说法作为故事的备选名称。逃犯自然对船长心存感激,不仅因为他提供的实际帮助,而且因为他表现出来的同情之心。他说:“得到别人的理解,这让我觉得非常满意。”但是,他们两人心知肚明,他待在船上会产生破坏作用。在他待在船上期间,船长做出了若干决定,发出了若干让船员们无法理解的命令,以便帮助他的新朋友。那名逃犯离开之后,船上恢复了正常状态,船回到正确航道。在故事结尾,船长与他的船员之间实现了“完美的交流”。他重新——可以这么说——获得了控制,重新建立了约束。尽管罗素在谈到康拉德时并未提及《秘密分享者》,我们实际上可以确定,他知道这个故事。年,他首次阅读了《黑暗之心》之后便做出决定,尽快阅读康拉德出版的所有作品。在他对康拉德的兴趣到达顶峰期间,《秘密分享者》出版。奥托琳肯定读过这篇故事;实际上,她在回忆录中提及它,其语境特别有意思:那个部分讨论男女之间的差异,讨论男女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自己情感的支配。她写道:“我发现,男人的观点——其中包括伯迪和菲利普的观点——常常是稍纵即逝的情感带来的结果。他们在情感受到影响的状态的言行并不表达他们的本意。”与之相比,女人“更令人难以捉摸,更克制……控制并且隐藏稍纵即逝的情感”。她继续说:我知道,我并不希望谈论我自已的情感,而是在秘密生活中面对它们。我怀疑,是否每个人都有秘密伴侣,都有第二自我,都有“秘密分享者”,以便讨论自已的想法和情感。我无法想象,谁可以在没有这种秘密伴侣的情况下生活下去。讨论让人互相厌倦。罗素对与康拉德见面的描述暗示,他将康拉德本人视为“秘密分享者”,视为“第二自我”,和康拉德分享“神秘交流”和内心的理解。两人都感觉到,陷入精神失常的状况可能随时出现,“灼热的内心世界”就在文明的表皮下面;这无疑是两人之间产生的移情作用的组成部分。但是,或者更重要的是,两人都感觉到,每个人都受到可怕的孤独感的困扰。在罗素对康拉德的描述中,这一点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与康拉德见面之后一天,罗素在给奥托琳的信件中强调:“我觉得,他在生活中非常孤独。”与罗素一样,康拉德在年幼时失去了父母,他7岁时母亲去世。他父亲与罗素的父亲类似,爱妻死后身心破碎,4年之后便撒手人寰。从那之后,康拉德由祖母和叔叔抚养。那时的家人在信函中说,他没有童年伙伴,整天埋头看书。换言之,他的童年与罗素的十分相似,而且似乎对他造成了类似影响。更有甚者,两人之间的相似之处扩展到对大海的喜爱。两人在不同时期,将大海描述为‘‘镜子”,似乎都认为,大海象征着一种巨大的自然力量,它给人慰藉,即是永恒的,又是非个人的。我们可以说,假如罗素是伟大的小说家,他可能成为康拉德那样的人物,以更强有力的方式,使用更精确的语言,探索自己内心的深处,超过他在实际生活中表现的能力。无论他何时尝试,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自传或者信件中,罗素情不自禁地描述自己的信念,然而自己的感受——表达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渴望的任务,他交给康拉德去完成。也许,这一点最有力的例证是篇幅较短的作品《艾米·福斯特》。如果说《黑暗之心》提供了罗素对精神失常的恐惧感的完美隐喻,那么,《艾米·福斯特》——罗素在谈到康拉德时详细讨论的另外一部作品——以非常动人的戏剧方式,表达了他的孤单感。罗素老年时告诉女儿凯特,他有孩子之前,常常做一个梦。“我想象,我在平板玻璃后面,就像水族馆里的一条鱼,或者变为无人可看的幽灵。我痛苦挣扎,试图与人接触,但是这不可能,知道自己命中注定,永远处于孤独无能的状态。”这就是《艾米·福斯特》的主人公扬科·古拉尔所处的情景。古拉尔来自一个东欧国家,在前往美国途中,他乘坐的海船沉没,他发现自己是唯一的幸存者。他被海水冲上英国海岸,但是他不会讲英语,周围的村民纷纷躲避。他们误解了他表示友好的手势,误解了他需要帮助的恳求,仅仅将他视为一个陌生人,也许视为一个精神失常的外国人。只有一个村民对他表示友好,她就是艾米·福斯特。她给他弄来食物,教他英语。后来,他和艾米结婚,生了一个儿子。他非常喜欢儿子,教儿子唱家乡的民歌,这让艾米很不喜欢,并且产生了疑心。有一天,他病了,高烧中开始使用他的母语,这让艾米非常恐慌,超过了可以忍受的限度。她领着孩子,不理会他的救命呼喊,离家而去。他伤心绝望,无法理解,为什么他钟爱的女人抛弃了他?为什么他不得不失去自己心爱的儿子?最后,他在孤独中死去。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suoe.com/llly/13398.html
- 上一篇文章: 罗索阅读了黑暗之心之后决定,尽快阅读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