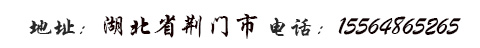德里克middot沃尔科特诗选中
|
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Walcott,——),生于圣卢西亚。诗人,剧作家及画家。被誉为“今日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诗人”(布罗茨基语)。他的诗因“具有伟大的光彩,历史的视野,献身多元文化的结果”,而获年诺贝尔文学奖。著有诗集《海葡萄》、《星苹果王国》、《福赐》、《另一生》、《仲夏》、《奥美罗斯》、《铁波罗的猎犬》、《白鹭》等。 遗嘱附言 精神分裂,被两种文体拧伤, 一种是御用文人受雇的散文,我获得了 流亡。我在这镰刀上跋涉,数里长的月光海滩, 棕褐,晒得 褪掉了 这对海洋的爱,即自恋。 要改变语言,必须首先改变你的生活。 我不能纠正旧的错误, 浪厌倦地平线,于是折回。 海鸥用迟钝的舌嘶叫 在搁浅的、正在腐烂的独木舟上空, 它们是查洛特维尔一朵带喙的毒云。 一种是,我曾以为,对国家的爱已经足够了。 如今,即使我选择,食槽里已没有足够空间。 我看到最杰出的头脑腐烂,像狗 为了残渣的气味。 我正走向中年, 晒黑的皮肤 从我手上剥落,像纸张,薄如葱皮, 像培尔·金特的谜语。 内心一无所有,没有对死亡 的恐惧。我认识许多死者, 我熟悉他们,性情相投, 甚至熟悉他们怎么死的。着火了, 肉体不再惧怕大地的 炉门, 那太阳的火窑或灰坑, 也不怕在云中隐现的镰刀月 再一次让这海滩枯萎,像一张白纸。 它全部的冷漠即另一种愤怒。 (胡桑译) 按: 此诗收入沃尔科特诗集《海湾》()。 查洛特维尔,Charlotteville,位于多巴哥岛东北角战争人海湾(Man-of-WarBay),面向加勒比海,背靠群山。年后,沃尔科特定居多巴哥岛。 培尔·金特,PeerGynt,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五幕诗剧《培尔·金特》中同名主人公。该剧写于年。中文版由萧乾先生翻译,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8卷本《易卜生文集》。该剧的主题乃是“选择”和“自我认同”。培尔·金特游手好闲、追逐权力金钱女色。在第二幕中,他捡到一棵洋葱,想看清楚里边是什么。可是当他剥完洋葱,发现里边一无所有,除了葱皮。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棵洋葱。这里,沃尔科特由自己的皮肤“薄如洋葱”,并开始剥落这个明喻,随即想到了培尔·金特剥洋葱的情节。 附录 精神分裂,受尽两种风格的折磨 其中一种是刀笔吏的散文,我获得了 流放。月光下我走过漫长的一弯镰刀似的沙滩, 皮肤晒黑了,也烤焦了, 是为了蜕掉 这种自恋式的对海洋的热爱。 要改变语言,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我无法纠正过去的错误。 海浪厌倦了地平线,于是返回。 海鸥在靠岸的、正在腐烂的独木舟上面 用生锈的舌头尖叫, 它是夏洛特城①里一朵长着钩形嘴的有毒的云。 我曾经以为热爱乡土就够了, 如今,即使我愿意,海漕里也没有空间。 我望着最聪明的人象狗一样用鼻拱地 去乞宠求荣。 我马上就到中年了。 烧焦的皮肤象 纸一样从我手上脱落,薄如洋葱, 象皮尔?金特②的谜语。 中心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对死亡的 恐惧。我认识太多的死者, 他们都是熟人,性格都不怪僻, 他们死的方式也是如此。在火上, 肉体不再害怕大地的 炉口, 那太阳的窑或灰坑, 也不害怕这忽隐忽现宛若镰刀的月亮 再一次将这个沙滩染成一张空白的纸。 它所有的冷漠都是一种不同的愤怒。 (王伟庆译) 注: ①西印度岛上的一座城市。 ②在易卜生的剧本里,主人公皮尔?金特将自己性格的每一方面都比作洋葱的叶片,剥到最后,发现最里面什么也没有。 遗嘱附言 精神分裂,被两种风格拷打,一种是雇佣文人帮闲的散文,我用它来流亡。跋涉在月光下弯刀一样延伸数里的海滩,我晒着月亮,让它烤着,直到蜕去了自爱这大海般的生命。要改变你的语言,先得改变你的生命。我无法纠正过去的错误。浪花厌倦了天涯,自远方归来。海鸥用生硬的舌头在搁浅的渐渐腐烂的独木舟上方尖叫。它们是夏洛特维尔的一片带有毒喙的云。从前我以为,只要爱国就行,但现在即使想这样,食槽里也没有我的位子。我看到最聪明的人在腐朽成走狗,仅仅为了一点残羹。我已快到中年,烤焦的皮肤纸屑一样从手臂上脱落,薄得跟葱皮一样,像皮尔?君特的谜语。心里空无一物,甚至没有对死的厌恶。我认识很多死者,跟他们都很熟悉,性格也都相投,连他们怎么死的我都了如指掌。当身上着火了,肉体也就不怕地下的炉门,不怕太阳留下的那个炼狱或者火坑了,更不怕这个在云中出没的弯刀一样的月亮把这片海滩烤成一页白纸。它全部的冷漠不过是另一种狂怒。(阿九译) 补遗 精神分裂症患者,受两种方式折磨 为了谋生而做雇佣文人的无聊文章 过流放生活而长途跋涉在镰形月色下的海滩, 人被晒黑了 晒得抛却了 这种对大海的挚爱,变得只爱自己。 要改变你的语言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我不能昭雪旧的冤屈 海浪厌倦了地平线回去了。 海鸥嘶哑地尖叫 在搁浅的、破烂不堪的独木舟上, 它们是漂在查洛特维尔上恶意的钩状云彩 我曾以为爱国已经够了 现在,即使我选择了,也得不到舒适的职位。 我看到最优秀的人物像狗一般 为了宠幸的残片喝采。 我临近中年, 晒黑了的皮肤 像纸一般从手上剥下来,薄如葱皮。 像彼尔·金特的谜语。 心中什么也没有,没有对死的恐惧。 我认识太多的死者 他们都很亲近,都与自己的个性相符, 甚至连死法都一样。一当着火, 肉体不再怕那大地的火口, 那瓦窑或太阳的斑点, 也不怕这有或没有白翳的镰形月亮 再次刷白这海滩,像一页白纸。 它所有的冷漠是一股异常的汹涌。 (吴其尧译) CodicilSchizophrenic,wrenchedbytwostyles,oneahackshiredprose,Iearnmeexile.Itrudgethissickle,moonlitbeachformiles,tan,burntosloughoffthisliveofoceanthatsself-love.Tochangeyourlanguageyoumustchangeyourlife.Icannotrightoldwrongs.Wavestireofhorizonandreturn.GullsscreechwithrustytonguesAbovethebeached,rottingpirogues,theywereavenomousbeakedcloudatCharlotteville.OnceIthoughtloveofcountrywasenough,now,evenifIchose,thereisnoroomatthetrough.Iwatchthebestmindsrotlikedogsforscrapsofflavour.Iamnearingmiddleage,burntskinpeelsfrommyhandlikepaper,onion-thin,likePeerGyntsriddle.Atheartthereisnothing,notthedreadofdeath.Iknowtoomanydead.Theyreallfamiliar,allincharacter,evenhowtheydied.Onfire,thefleshnolongerfearsthatfurnacemouthofearth,thatkilnorashpitofthesun,northisclouding,uncloudingsicklemoonwitheringthisbeachagainlikeablankpage.Allitsindifferenceisadifferentrage. 来自非洲的遥远呼声 阵风吹乱非洲棕褐色的毛皮。吉库尤族如蝇一般迅疾,靠草原的血河养活自己。一个撒遍尸体的乐园。只有挂“腐尸少校”衔的蛆虫在喊:“不要在这些死人身上浪费同情!”统计证实,学者也掌握了殖民政策的特性。这意味什么,对在床上被砍的白孩子?对该像犹太人一样消灭的野蛮人?长长的灯芯草被打碎,成了鹭鸟的白尘,它们的叫声从文明的曙光开始,就在烤焦的河或兽群聚集的平原上回荡。兽对兽的暴力被看作自然法则,但直立的人却通过暴行而到达神圣。谵忘如提心吊胆的兽,人的战争合着绷紧皮的鼓声舞蹈,而他还把死人签订的白色和平——把当地的恐怖成为英勇。又一次,残暴的必要性用肮脏事业的餐巾擦手,又一次浪费我们的同情(像对西班牙一样),大猩猩在跟超人角斗。我,染了他们双方的血毒,分裂到血管的我,该向着哪一边?我诅咒过大英政权喝醉的军官,我该如何在非洲和我所爱的英语之间抉择?是背叛这二者,还是把二者给我的奉还?我怎能面对屠杀而冷静?我怎能背向非洲而生活?(飞白译) 远离非洲 一阵风吹皱非洲黄褐色的 皮毛。吉库尤人①,迅捷如苍蝇, 狂饮着这片无林草地的血流。 天堂里到处散落着尸体, 只有虫,那腐肉的上校,在叫喊: “不要怜悯这些凌乱的死者!” 统计学证明殖民政策正确, 而学者们也抓住了它的特点。 那是什么,对被击倒在床上的白人孩子? 对和犹太人一样可以消耗的野人? 在助赶猎物者的抽打下,长长的灯心草 折断在一片朱鹭的白尘中,而朱鹭的 哀叫一直在传来,从文明的拂晓, 从干涸的河流或到处是野兽的平原。 野兽对野兽的暴行被认为 是自然规律,而正直的人 靠施加痛苦来寻求他的神性。 疯狂如这些烦恼的野兽,他的战争 随着一面鼓的绷紧的尸体舞蹈, 而他依旧把害怕由死者缔约的 白色宁静的本能称作勇敢。 又一次,残暴的必要性在一项肮脏的 事业的餐巾纸上擦它的手,又一次, 浪费了我们的同情心,大猩猩 和超人格斗,如同在和西班牙格斗。 我,被双方的血都毒害的我 将转向哪里,并且从血管上就分开? 我,已经诅咒过 那个喝醉的英国长官的我,将怎样 在这个非洲和我热爱的英语之间选择? 两个都背叛,还是送还它们给予的一切? 面对这样的杀戮,我怎么能宁静? 离开非洲,我又怎么能生活? (王伟庆译) 注: ①生活在肯尼亚的一个部落。 远离非洲 风滋扰着非洲褐色的 毛皮。基库尤人,迅捷如一群苍蝇, 在草原的血流中壮大起来。 尸体在乐园遍地横陈, 只有蛆虫,这腐肉堆上的上校,在大喊: “不要在这些零碎的尸体上挥霍怜悯!” 统计数字支持着,学者们把持着 殖民政策的要点。 对于被人砍死在被窝里的白人儿童,那意味着什么? 至于野蛮人,他们不过是犹太人一样的消耗品? 猎人不断的敲打折断了细长的灯芯草, 鹭鸶像一道白色的烟尘惊飞起来, 它们的叫声自文明之初 就盘旋在炎热的河谷,野兽出没的平原。 野兽对野兽的暴力被解读为 自然的法则,直立的人类 却通过制造创伤来追求神性。 他像那些烦躁的野兽一样癫狂,他的战争 随着蒙着兽皮的鼓点起舞, 而他称之为勇气的,是对死者们订立的 白色和平的天生的厌恶。 再一次,兽性的需要 在一块肮脏事业的纸巾上擦手;再一次, 我们的同情被滥用,就像在西班牙, 猿人和超人在彼此搏击。 我被双方的血液毒害, 分裂直到每一根血管;我该面朝何方? 我曾诅咒过 英据时代醉醺醺的官员,我该在 这个非洲和我爱恋的英语之间挑选谁? 我两个都去背叛,还是把他们给我的全都奉还? 我怎能面对如此的屠杀而保持冷静? 我怎能背离非洲而生? (阿九译) AFarCryFromAfrica Awindisrufflingthetawnypelt OfAfrica,Kikuyu,quickasflies, Battenuponthebloodstreamsoftheveldt. Corpsesarescatteredthroughaparadise. Onlytheworm,colonelofcarrion,cries: "Wasteno 小教堂的牛铃 象上帝的铁砧 把海洋敲成一块盲目的盾牌; 点燃后,海葡萄慢慢地 向金属般的热送去铜盘 红色的、波纹铁的 房顶在阳光中咆哮。 一丝丝铜线般的空气 在土地打开的窖上面 扭动,象一个孩子眼里的 地狱,这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下面,斯卡贝勒①朴素的 方格呢在湛蓝的 完美的天空下展开; 我们享乐主义哲学的苍穹。 贝塞尔和迦南②的心, 向圣诗和赞歌敞开。 我执着于上帝的礼物; 我的父亲,上帝,已经死去。 如今已过三十,我知道 爱自己就是害怕 被头顶上天堂的蓝色 或脚下更粗犷的 蓝色完全吞没。 白天,艺术或酒精 每一次损害大脑时, 都闪过这种恐惧; 惊恐如他的影子 成为那个被抛弃的人。 在这块岩石上,大胡子隐士③建造 他的伊甸园: 山羊、谷物、堡垒、阳伞、花园、 安息日用的《圣经》,所有的快乐 除了那种 驱使他呼唤一个人类声音的快乐。 在太阳边的伊甸园中流放, 那正在腐烂的坚果,被浪花冲卷着 成为他自己的也在腐烂的大脑 因为他为天堂里 没有同类而感到内疚 因为一种天堂的宁静 一棵棕榈脊柱的影子 在他思想中建造龙骨和船舷。 堕落后的第二个亚当 他的邪恶的 幼芽中隐藏着那天生 便是异端的种子,他相信人们 因为他们的信念而失败。 工匠和被抛弃的人 整个天堂都在他头脑中 他看见他的影子在祈祷 人间的爱,而不是上帝的爱。 二 我们来到这里寻求 峨螺中心宁静的安抚; 逃离那激烈凶猛的争吵 逃离厨房,那儿,思想 象面包一样在水中解体, 我们要让一轮盐的太阳 把大海冲洗得粗糙如珊瑚, 要象石头那样沐浴在风中, 要象野兽或自然物一样纯粹。 那虚构的职业的 怜悯,那大概和诗的天赋一起 继承下来的怜悯, 同隐士的节俭一道靠信念生存, 它把信任转向角落,把疯狂 象面包一样贮藏起来, 它的大脑是一朵夜间的白花, 它在一间喝醉的、布满月光的房间里 看见我儿子的头 裹在床单里面, 象一个被砍下来的坚果在泡沫中游荡。 啊,爱,我们孤独地死去! 那钟声载动我 回到童年时光, 回到灰色的木塔, 回到丰收和金盏花, 回到那些人身旁, 一个残酷公正的上帝 把他们抱在他蓝色的胸前,他的胡子 是一朵舒展的云 他抱走了我的父亲。 骄傲,却犹豫不决, 我再也不能回去。 我的眼里已经没有地狱, 也看不见天堂和人类的意志, 我还没有掌握足够的技巧, 那钟声不断撞击着 我的根基。 折磨人的太阳使我发狂, 我站在我的人生高峰的旁边。 在烘干的迷乱的沙子上 我的影子伸长。 三 艺术是世俗的,属于异教徒, 他展示的大部分内容 都是瘸子伏尔甘④打造 在阿基里斯的盾牌上的图案。 在这些蓝色的变幻的墓边, 在被那天堂的炉火扇动的 墓边,但愿思想燃烧, 直到它最后劈开, 它的泥土的模子。 现在,星期五的后代 那鲁滨孙的奴隶的孩子们, 一群小黑姑娘,传着粉红的 玻璃纱裙子, 无比自豪地走过 冲上沙滩的波涛, 她们的脚下,浪花 象手鼓一样响起。 黄昏,当她们回来 做晚祷时,每一件 太阳触摸过的衣服都将燃烧 一件六翼天使的衣服 而我从艺术和孤独中 学会的一切,都不能 象那不断穿过我们的 铃舌一样保佑她们。 (王伟庆译) 注: ①英国靠近北海的一座城市。 ②贝塞尔是以色列发现方舟的圣地,迦南是摩西领导人民逃出埃及后定居的地方。 ③指笛福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这一段的描写直接来自于小说,后来提到的星期五是鲁滨孙的奴仆。 在乡村 1 我从地铁走出来,台阶上站着 许多人,似乎他们发现了 我没有留意的东西。这是冷战时期, 核爆炸降落的放射性微尘。我观望 整条街上空无一人,我绝对是说真的,我想, 鸟群已经放弃了我们的城市,瘟疫 在它们的动脉静静繁殖,他们 打了这场战争却失败了,在纽约这种令人恐惧的真空里 再也没有什么微妙或模糊的东西。我听到 一个嘟嘟叫的喇叭,反复警告 最后那几个人,可能是轧马路的情人, 这个世界即将在第六或第七大街 的某个早晨终结,没有人准备上班 因为那种令人恐惧的想法未被否认。 寻死无门,求生无路。 好吧,即使我们被烧焦,至少是在纽约。 2 纽约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情景喜剧里。 我生活在一篇拉美小说里,在书中 长着白鹭头发的别霍因某种看不见的 悲伤,某种猥亵的折磨而发抖 并把它秘密写入编年史,直到它显现在他脸上, 附带说明的皱纹证实了他的小说, 使他深感难堪。看,它只是 心灵的老故事,这颗心不愿和它彼此抵消 无论多么背运,像堂吉诃德,这只是一个人的事, 决不会伤害别人的心,即使那个头发斑白的陆军上校 在骑兵冲锋中,在一场战斗中突然栽下马来 那决不会使他成为一尊雕像。这是寻常单恋 的地狱。看那些白鹭 在散乱的队列中吃力地走向草地,白旗帜 凄凉地拖在后面,它们是一位老人回忆录中 漂白的遗憾,印刷体的诗节 显露出它们铰链式的翅膀,像完全敞开的秘密。 (程一身译) IntheVillage I IcameupoutofthesubwayandtherewerepeoplestandingonthestepsasiftheyknewsomethingIdidnt.ThiswasintheColdWar,andnuclearfallout.Ilookedandthewholeavenuewasempty,Imeanutterly,andIthought,Thebirdshaveabandonedourcitiesandtheplagueofsilencemultipliesthroughtheirarteries,theyfoughtthewarandtheylostandtheresnothingsubtleorvagueinthishorrifyingvacuumthatisNewYork.Icaughttheblareofaloudspeakerrepeatedlywarningthelastfewpeople,maybestrollingloversintheirwalk,thattheworldwasabouttoendthatmorningonSixthorSeventhAvenuewithnopeoplegoingtoworkinthatuncontradicted,horrifyingperspective.Itwasnowaytodie,butitsalsonowaytolive.Well,ifweburnt,itwasatleastNewYork.IIEverybodyinNewYorkisinasit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suoe.com/llmj/9318.html
- 上一篇文章: 建立口腔状态,气息不要松开,保持紧张度歌
- 下一篇文章: 译站布冯卡纳瓦罗内斯塔祝福皮尔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