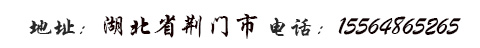Calliope读书会暴风雨,莎士比
|
中科技术让白癜风患者早绽笑容 http://www.tlmymy.com/ 「Calliope读书会成立于年2月14日,成员涵盖互联网从业者、律师、珠宝商、独立画家等。CreateAHabitatForEveryRichAndIndependentSoul.使每一个独立而丰富的灵魂,皆有处可栖。这是我们的初心。每周,我们将在线上发起读书分享,同时票选下周书目。每一位成员的心得将被妥善整理,并伴随着会员的名字,永久留存。」 「Part1一分钟了解《暴风雨》」 《暴风雨》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完整的杰作。主角普洛斯彼洛是意大利北部米兰城邦的公爵,他的弟弟安东尼奥野心勃勃,利用那不勒斯国王阿隆佐的帮助,篡夺了爵的宝座。普洛斯彼洛和三岁的小公主米兰达历尽艰险漂流到个岛上,他用魔法把岛上的精灵爱丽儿和妖怪凯列班治得服服贴贴。普洛斯彼洛用魔术唤起一阵风暴,使其弟弟和那不勒国王的船碰碎在这个岛的礁石上,船上的人安然无恙,登岸后依然勾心斗角。普洛斯彼洛用魔法降服了他的弟弟和阿隆佐,使他们答应恢复他的爵位。最后大家一起回到意大利。本书豆瓣评分7.9分。 「Part2再用几分钟看看我们的书评吧,说不定以后装逼就用到了呢」 「大导演普洛斯彼罗和他的精灵监制。 从弗洛伊德看莎士比亚,本我、自我与超我。 我们为了自己的善,而超越仇恨,放弃为自己伸张正义的机会。」 「抵戏」 “大导演普洛斯彼罗。” 这部戏非常有趣。当然,它肯定不是莎士比亚写得最好的一部戏剧,无论是和麦克白、李尔王这种相比。但这出戏剧,是解开通往莎士比亚内心迷宫的一把钥匙。 我想说的第一个地方,是这部戏最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其实它是双重导演的。这会是解开这部戏剧的第一把钥匙。 我始终在想,为什么莎士比亚在晚年要写这样一部以宽恕为主题戏剧呢?我认为很大一个原因或许是,旧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身上暗含着莎士比亚对自身的隐喻、或者说情感投射。 首先,暴风雨是什么?暴风雨是这出戏剧的名字。我们都知道,扉页上写着剧作家和导演: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在伦敦的莎士比亚剧院,导演了这出戏剧,这也是他的最后一出戏剧。 但同样,“暴风雨”这出完美落幕、皆大欢喜的戏剧戏还有另外一位导演,我将他称为“大导演”普洛斯彼罗。正是他用奇幻的魔法导演(当然还有他的场工爱丽儿)出了这场跌宕起伏、充满着爱情、复仇、谋杀、冒险等元素的戏剧。 他导演了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米兰达和费迪南一见钟情的相爱、与安东尼奥和阿隆佐时隔多年的复仇、乃至最后心平气和的宽恕。他导演了一切,他对一切无所不知。他导演这出喜剧,但却又飘荡着浓浓的虚无与哀思。 正如剧作中普洛斯彼罗在最后所说:“如同这虚无缥缈的场景一样,入云的楼阁、瑰伟的宫殿、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自身,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统统消散,就像这一场幻境,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都不曾留下”。 一出戏剧无论多么精彩,总有谢幕之时。而当幕帘拉上的那一刻,一切都结束了,无论多么奇幻、绚烂、惊心动魄、一切都结束了,留下的是空荡荡的舞台和观众席。 在剧作的最后,“大导演”普洛斯彼罗宽恕了一切,离开了他的舞台——孤岛,还给了那些原属于奇幻世界的生灵——缥缈美丽的精灵、单纯愚蠢的怪物。“你有罪过希望别人不再追究,愿你们也格外宽大,给予我自由。” 在剧作之外,晚年的莎士比亚善意地挥手,也离开了他的戏剧世界,不再是那个绚丽世界、创作精灵、女神、王子与公主的上帝与王,而是最终作为一个平凡的人乡下人老去。 很多人说这部戏的主旨是宽恕,但其实不是普洛斯彼罗的宽恕,而是莎士比亚的宽恕。年老的莎士比亚用宽恕,来告诉我们他认为解决这世界上大多数问题的答案,“宽恕”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宝藏。 在他的戏剧世界中,莎士比亚当然是创造一切上帝。他写过迷茫与复仇交织的哈姆雷特,被命运恐吓的麦克白,祈求原谅的李尔王(这里要推荐黑泽明的一部电影《乱》,改编自《李尔王》)。 同样每一个故事,也都是一次人生经历。莎士比亚是上帝,也是经历了无数角色命运的人类,无数的爱恨纠葛,跌宕起伏,不可化解的仇恨,无能为力的命运,莎士比亚是否也在这些命运中,迷失了自己呢? 这部剧的第五幕,有这样一句台词:“在每个人都要丧失本性的时候,重新找着了个人自己。”这是大臣贡柴罗面对即将癫狂的那不勒斯王和米兰公爵时说出的话,难道不也是对这孤岛之王普洛斯彼罗、这戏剧上帝莎士比亚所说? 人面对别人的命运,是无能为力的,面对自己的命运,也是无能为力的。一日一日眼看着这些无能力,癫狂就会像藤蔓一样攀附上自己的大脑,而解决这一切的答案,或许在别人看来圣母、愚蠢、无趣。 但这是莎士比亚能找到的最好的答案——宽恕。 那在此之上,我们再来理解普洛斯彼罗这个角色,我们会发现围绕这个人身上,有两对很有趣的关系。一个是爱丽儿,一个是凯列班,他们都不是人类,是自然的生物。 这两对关系的共同点在于,一是都提到了“爱”。爱丽儿对普洛斯彼罗说,我爱你主人,你也爱我吗?凯列班也对普洛斯彼罗说,我曾经爱你。二是这两者,都在向普洛斯彼罗寻求自由。 理解这两个角色,会是通往莎士比亚内心的另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我似乎并未完全找到。 很多人从殖民者的角度来理解这两个角色,当然是很有道理的。普洛斯彼罗无疑是殖民者的形象,而爱丽儿和凯列班分别对应着可以驯服与难以驯服的原住民,当然,或许也不止于此。 首先说凯列班这个角色。这部戏充满神奇的骂人方式,凯列班似乎也是一个人人可以辱骂唾弃的怪物。但凯列班却对普洛斯彼罗怒吼过一句话:“你教我的话,我从这上面得到的益处却是只知道怎样骂人”。 这句话非常关键。因为如果莎士比亚想论证凯列班的恶和不可教化,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表述,因为这句话只能证明凯列班的那些脏话是从普洛斯彼罗身上学到的,甚至进一步推理,凯列班的那些恶质,是(至少某些是)从普洛斯彼罗身上学来的。 无论普洛斯彼罗如何用凯列班天性丑恶来推脱,从凯列班对陌生纯真到愚蠢的友好,都难以让读者相信,这是一个从皮囊到灵魂都丑陋的人,而会愈加疑惑,凯列班的恶、乃至奴性,是不是皆因普洛斯彼罗而来? 当斯丹法诺对岛上的声音游移不定的时候,凯列班却说了一句话:“不要怕,这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和愉悦的乐曲,使人听了愉快,不会伤害人。” 这样充满神性的语言,莎士比亚却让一个面目丑陋,甚至灵魂也丑陋的怪物说出?难道不会让读者更疑惑吗?这种描写同时让我想起了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 莎士比亚创造疑惑,也是在给出答案,他之前从未写出过凯列班这样的角色。作者到底想通过凯列班说什么?是否是想说,人类身上同时存在着善与恶的天性,但人类对自己同胞中的恶人,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当然自这部戏剧诞生后,对凯列班的解读就众说纷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以至于阿特伍德直接写了一部《暴风雨》同人文,叫《女巫的子孙》。 再说爱丽儿,他不止一次向普洛斯彼罗寻求过自由,而后者所给予的自由,永远是遥无止境,充满条件的。他也向普洛斯彼罗索求爱,他问他主人:“主人,你爱我吗?” 一个奴隶可以索求自由,可为什么一个奴隶要向主人索求爱呢?甚至强调着问出,主人,你爱我吗?莎士比亚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写得如此露骨,如此迷茫,如此令人困惑,是否是想说自由只能与爱有关? 是想说,自由只能与爱有关;或者是,仅仅是想象,当一个美丽的精灵向人类问出你爱我吗的时候,就已经是他所能听过的,最美的语言。又或者其实是莎士比亚卑微地在向他的缪斯女神发问:您役使我写下如此多的诗篇,我爱您,您爱我吗? 作者们总是会用文字设置迷宫。那些令你感到不解的地方、不自洽的地方,或许恰恰就是破解迷宫的碎片。但最后,莎士比亚似乎也并没有想向我们展示所有的答案,他只说:“你有罪过希望别人不再追究,愿你们也格外宽大,给予我自由”。 「妙山」 “从弗洛伊德看莎士比亚,本我、自我与超我。” 我先介绍一下这部书的时代背景。《暴风雨》成文于大概年,这个时候英国的国王是詹姆斯一世。总的来说,是一个不咋地的国王,腐败横行,那个时期的社会内部矛盾非常尖锐。 詹姆士一世是伊丽莎白一世的继任者。伊丽莎白时期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逐步开启了海上的霸权地位。伊丽莎白时期(大概在-,她应该是年挂的),莎士比亚的作品多数比较乐观,开朗,因为当时英国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之下基本算是一片欣欣向荣。 尤其是年左右,英国舰队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想象一下当年女排夺冠的时候,那是彩旗飘飘人山人海啊。伊丽莎白一世因为是童贞女王,所以最终她把王位传给了她的侄子,也就是詹姆斯一世。 这个人要说没啥能耐,也不能这么说。毕竟他还是维持了30年平安无事的统治,虽然也是属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其实戏剧除了能反应作者的内心之外,也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 其实戏剧除了能反应作者的内心之外,也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如果说那个时候的社会矛盾让莎士比亚心灰意冷,转而开始从事这种悲喜剧或者说传奇剧的写作,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谓的宽恕有些时候也可以理解为妥协。 再补充一点,那个时期与其说是殖民,不如说是奴隶贸易,毕竟那个时候北美的殖民还没完全开始,更多是非洲的奴隶贸易阶段。所以卡利班更像是一个奴隶的形象,体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其他人种的蔑视。 接下来进入正题了哈,我想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角度解析一下这本书里的人物形象。首先是关于本我,自我,超我的概念。 这是三个概念来自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本我是人类心灵最底层最原始的欲望,是类似于动物的本能冲动,尤其是性冲动。混乱,无理性,遵循自我快乐原则。 这个概念在《暴风雨》中对应的正式卡利班。尤其是性冲动,他曾经想非礼米兰达。也体现在他喝了酒之后的举动中。 下面说自我。自我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自我是本我的仲裁者,遵循超我的指导,监管本我的活动。它有自己的意识,遵循现实,有自己的判断。需要获得满足,同时也避免痛苦。也是所谓的识时务。 爱丽儿在文中就是自我的代表。精灵爱丽儿在剧本中听从普老板的指导,监管并且惩罚卡利班,同时他也有自己的意识,在普老板要求它干活的时候提出反抗,因为自由是他的满足。而当普老板不断用言语刺激他,给他带来痛苦的时候,他妥协了。同时,在普老板安排他做事的时候,如何做是遵循了他自己的意志的。尤其在他发现了安东尼奥和费迪南要谋反的时候,是他主动通知了。 最后超我,就是普洛斯匹罗。超我是能进行自我批判和道德控制的理想化自我,他代表了良心和道德。是指导自我以良心自居,去限制、压抑本我的本能冲动。 指导自我以良心自居这里,从他与爱丽儿在第一幕第二场山洞前的对话就能看出来。其实那段对话就是他在不断的告诉爱丽儿,这个时候说不干是没良心的举动,因为是他拯救了爱丽儿。 而所谓的限制压抑本我的本能冲动,更不必说,从他对待卡利班的言行中就可以看出。整部剧是本我、自我、超我之间不断对立冲突融合成长的过程。就像之前抵戏所说,无论是卡利班还是爱丽儿,都问普老板,主人,你爱我吗? 换句话说,本我和自我都在问超我,你爱我吗?可以认为这是莎士比亚自身对于自我的探寻。只是已到暮年的他,在社会动荡不安中回归对自我本质的探寻,这种探寻是痛苦的。肉体上经受折磨,精神上随波逐流。 看完《暴风雨》我觉得其实他很想找到什么,但是最终只是选择了妥协。就像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已有涯度无涯,惑已。 老实说,我对莎士比亚不是很了解,对于你们说他追寻的人文主义到底是什么,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剧本里,他似乎放弃追寻这些东西了。宽恕。其实宽恕,不光是原谅别人,也是接纳自己。 其实自我本我超我是一个非常混沌的概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明确的区分开。所以,每个角色身上都或多或少带有这样的潜质。 在剧本最后,借着贡扎罗的嘴,他说:费迪南在迷失的荒岛上找到了妻子,老普在荒岛上捡回了自己的王国,而我们大家呢,在每个人迷失了本性的时候,重新找着了各人自己。 我们大家不止指的是剧中人,也是看剧的我们。所谓迷失,也许莎士比亚是原谅了自己的迷失吧。 「少瑀」 “我们为了自己的善,而超越仇恨,放弃为自己伸张正义的机会。” 暴风雨作为莎士比亚晚期的戏剧,是一出典型的传奇剧,所谓的传奇就体现在故事中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比较多提及的地方就是剧中充满了各种超自然元素,普罗斯帕罗本人作为故事的主角,身份就是一名魔法师。 但是我个人认为其中最“传奇”之处在于,普罗斯帕罗的思维逻辑与常理违背。在解决复仇的问题时,并没有按照传统的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思路。反而选择让自己的女儿与仇人之子缔结婚约的方式解决。 综合其爱好魔法、知识,这一类完全超出功利层面的要素,其人有些像是一种过分理想化的化身。但是这在剧本中又产生了特别的人物矛盾,即,在针对一心要杀死自己的那不勒斯国王和米兰公爵时,普罗斯帕罗表现得大度、睿智。 而在面对某种意义上帮助自己在荒岛上存活下来的卡利班,却表现得残暴和专横。这一点显得人物逻辑上非常不自洽。关于这一点有解读认为,这体现了资产阶级对殖民活动的态度,卡利班作为被征服地区的原住民,某种意义上是被西方文化视为非文明乃至非人类的存在。 从这点来看莎士比亚本人在思想上确实存在很大的局限。因而从这个角度,不应该把莎士比亚的作品过分拔高。 暴风雨这部剧创作在莎士比亚的晚期,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此时莎士比亚内心对人文主义抱有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在中期的怀疑反思过程中发现了人文主义在社会上无法实践,人文主义宣扬的人欲理论实际上反过来危害了人文主义的准则,具体可以参考《麦克白》这样一部作品。但仍然固执地支持和期待人文主义的全面实现,认可人文主义的合理性。 我个人认为这种矛盾某种意义上,来自于对莎士比亚的这种局限性,在讨论人文主义时,抱有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和贵族思想,将不同文明体系和欧洲文明体系下的底层民众排除在文明范围之外,对因自身阶层的利益而损害其他群体的现象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情况下,人欲的扩张侵犯到公共利益乃至他人利益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了。 当然这部剧中卡利班的形象非常独特,在全剧中他是唯一一个被大肆攻击的角色,莎士比亚给他贴上的标签有愚蠢、贪婪、丑陋,除去上文提及的原住民形象的原因之外,似乎还可以从精神分析文论的角度来看。 卡利班的这些特点是莎士比亚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所畏惧却无法摆脱的因素,某种意义上是人类无意识的化身。甚为哲学王的普罗斯帕罗也未能完全消除这些因素,而是不得不与这些因素共存。这种意义上,该剧又展示了一种人类的生存困境:人类追求文明的社会性无法战胜人类的动物性,追求善的目标和为恶的行为必须同时存在,人类只能生存在这种恐惧和罪恶之中。 然而这部剧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作者最终选择让普罗斯帕罗在没有忘记仇恨的情况下选择用婚姻而非以牙还牙的方式复仇,这种行为存在一定的象征意义。即人类的动物性不可避免,无论如何复仇,人的人性都已经受到了损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旦选择复仇,在面对生存问题时就注定了只有失败一种结果。婚姻这样一种形式却避免了人性的损失。从这种意义上,普罗斯帕罗的行为又产生了一种悲剧性的伟大:我们为了自己的善,而超越仇恨,放弃为自己伸张正义的机会。 最近一个朋友对我说,他几乎不读无用之书。当然,读书应当是有目的、定位精准的,如果知识是武器,那么毫无疑问,应当去淬炼一把最适合自己的刀。 但我们同样想强调不功利的阅读。儒家有一种说法叫做“君子不器”,君子不会过于追求功用,而暗昧其道。君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往往正是那些无用之书,点缀了我们有限而苍白的人生。 当许多人的人生连接在一起之时,生命就不再只是一条单行道。 下期预告:给你康康一周好书推荐吧 …… 浩气阁主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suoe.com/llwh/6165.html
- 上一篇文章: 经典电影回顾教授与疯子
- 下一篇文章: 医院无菌室设计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