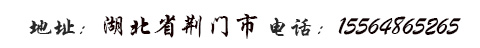漫步里约,地球另一端的光与暗
|
经历了26小时飞行,抵达里约加莱欧机场时,并没有过往来到异大陆时的兴奋感。长途飞行让人疲惫不堪,坐上出租车前往市内,两边堆满了五颜六色大型集装箱。稍后经过一座桥,司机说左边就是罗纳尔多过去踢球的地方,我的目光却锁定在右边,满是黑水的大型垃圾堆放站就那样裸露在街面,隔着车窗似乎都能闻到里面的恶臭。 里约热内卢,葡萄牙语的读法是ひ(这个音中文发不出来)欧德-夏(三声)内洛,意为“一月之河”。 我把自己安顿在一个叫largodomachado的地方,街面上到处都是涂鸦,别人投来的目光也不那么友善。我牢记当地人george的忠告:别去海滩,别露富(虽然也没什么可露)。 george告诉我,“这里所有的警察都像退役后的罗纳尔多一样胖,整天喝啤酒吃烤肉,追不上那些灵敏的黑人小孩。”我对此深信不疑,刚才我们途径一处警察局,门口全是荷枪实弹的壮汉。“警察的装备这么好?”“那是保镖公司。”“保镖公司?为什么会在这?”“警察前几天端了一个毒贩窝,怕对方报复,请保镖公司保护自己。” 来了里约,不去海滩又是不可能的。 在copacabana,我兴奋地寻找着naraleao过去的房子,每每左顾右盼之后才拿出不那么张扬的富士相机,按下几张充满青春活力的照片。中午时分,我在garotadeipanema坐了下来,这里原名维罗索酒吧,维尼修斯和若宾过去屡屡在此抽烟喝酒,互诉衷肠,他们被一位名为皮涅罗的19岁姑娘吸引。姑娘住在依帕内玛的蒙特内格罗区,经常会从酒吧前走向沙滩,或者进来为妈妈买一支雪茄,若宾和维尼休斯以她为灵感创作了《依帕内玛姑娘》,这首歌作为bossanova名曲,后来风靡世界,人尽皆知。 虽然传闻如此,当地却有不同说法,“皮涅罗只是以给妈妈买烟为名,在酒吧里随便去找个男人一起快活。”这个说法似乎更符合巴西人的脾性,只是环境无法让人判断出当时的情况,现在的维罗索酒吧,是一家卖铁板烧的半露天餐厅。 穿着红色马甲,蓝色围裙的胖侍者穿梭而过,到处都是烧肉的香气和烟雾,老板指着店铺深处的乐谱和双人席,“那是维尼休斯过去创作过的地方哦。”铁板烧很快端了上来,是一个人绝对无法吃完的量。巴西盛产肉类,肉的品质绝对没得说,很多时候烤肉并不抹油,只靠肉本身渗出的丰富油脂即可。 饭后沿着维尼休斯大道散步,拐进了路边的唱片店tocadovinicius,买下了两张旧唱片。去柜台结账时,正在记笔记的店主阿尔贝托抬起头,露出令人舒心的微笑,店铺另一侧,阿尔贝托满头白发的妻子正在整理唱片。“我想把里约诞生的音乐传达给后世,所以放弃了教师工作在这里开店。” 阿尔贝托喜欢bossanova,这种音乐反映出深深的saudade。saudade,在葡萄牙语和加利西亚语中代表“乡愁”“憧憬”“思慕”,是巴西艺术表现的中心,以bossanova来讲,在“充满怀念”,“幸福”这些正面情绪中加入悲伤的曲调,描绘出悲喜交加的感情。 阿尔贝托夫妇把我送出门,告诉我这条大街上还有哪些可逛的地方,看到这里到处是友善的人,对海滩的戒心也放松了很多,很快就来到了另一侧的ipanema。 copacabana和ipanema,两处海滩同样是名声在外,气氛却颇有不同。前者到处是观光客,交通拥堵,有人雕出了精细无比的沙雕,“tiagosilvario-paris”,当你和巴西国家队队长的雕像合影后,突然有人跳出来拦住去路,“拍照要收5雷亚尔!”就像是国内一些景点的状况。ipanema旁边都是高级酒店,人也不多(后来我发现周末人潮完全是另一回事),有一些像是本地富人的人在慢跑。 海滩附近有一座巨大的贫民窟,很多无所事事的人白天从里面出来,去海滩上偷盗抢劫。里约的贫民窟有多危险,在《速度与激情》《上帝之城》等电影中有很直观的展示,但也有很多外乡人进到里面,和本地人谈笑风生。这其实很好理解,贫民窟分为警察控制和毒贩控制,前者可以进入,有些地方甚至还装了观光缆车,后者则充满危机,最近刚有新闻称,一位警察误入贫民窟吃到流弹。前面说到警察雇保镖保护自己,就是因为他们接到政府指示,端掉了一座毒贩控制的贫民窟,现在进去还可以看到被手榴弹炸塌的墙,以及当作掩体被打得千疮百孔的大众面包车。 我喜欢ipanema多过copacabana,往后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去海滩,吃9雷一只的番茄汁煮螃蟹,很幸运一直没有人盯上我的钱包,里约是一座自由且友好的城市。晚上去住处附近的福建人餐馆吃饭,听到我的感悟,他们总是很不屑,“那是因为你没有在这里长住,我们出去从来都是带两个钱包,有人来抢就主动把钱少的那个给他。”“那他们不搜身么?”“从来不会,只要你主动交上钱包!”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令我信服。 真正让我有些担心的是,有一天我从巴西利亚回里约,那一晚正好是世界杯足球赛的半决赛,就在我从酒店大门出来的时候,德国队刚刚第六次攻破巴西的球门。巴西球迷会闹事么?网上到处都是这样的消息,我约的出租车也头一次失约了,没有停在约定的地方,好在另一位看上去十分和蔼的司机请我上车,在接近午夜的时候,我又一次降落在了加莱欧机场。 一个戴眼镜的胖司机向我索要雷,看在他是正规出租车和我想尽快回到住处的份上,我没侃价。聊起那场比赛,他做出大拇指向下的动作,表示自己看到3比0就出来拉活了。一路没人闹,也没人哭喊,里约出奇平静。其实我早该知道这点,在中场休息时罗纳尔多像往常一样镇定地画着战术板,给电视观众分析克洛泽打进的那个球时,我就该知道了。这个球不但杀死了巴西,还让克洛泽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超越了罗纳尔多,但那又如何?巴西人赢过5次冠军,当你清楚胜利的感觉,失败是不会让你失去理智的。 在体育上,我们也清楚胜利的感觉,但有人依然会为了一两句话,在大赛期间抓着对手不放,认为他们损害了某种自尊。这个阵营越来越庞大,直到容不下其他声音,这与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相同。体育是和平年代的战争,放在这里一点不假,只不过有时候它并不是形容比赛的激烈程度。 在里约的生活越来越规律,我每天白天出门,晚上回来吃饭并喝上一杯caipirinha,坐出租车和吃晚餐成了我与当地人交流的固定渠道。“中国人在这里挣钱很容易,因为这里的人太懒了。”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巴西的手工业极其落后,来这的中国人,大多发了点小财,但他们也过得如履薄冰。因为有些钱的来路不正,不敢存到银行,放在家里一但被抢,就前功尽弃。我听说有些中国人把同胞家里有钱的信息透露给巴西人,巴西人去抢,他们再提成,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安全,我开始从同胞的控诉中了解到现实的残酷。 去了巴西利亚,我总是光顾一家中餐馆,店主是北京移民。他有时懒得开门,晚上8点到店里,大门紧闭,敲开了才很不情愿地做上两桌。“来这就是想过得自在点,做生意太麻烦,少挣点钱也没什么影响。”巴西利亚的中国人比里约和圣保罗少得多,这家中餐馆成了在地中国人的社交场所,使馆的人也经常到访,有一次孔子学院讲汉文学,还请了这位老板去。这大哥的学历可能不超过中专,在巴西都给外国人讲上汉文学了,我有点理解他不那么爱做生意,可能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文人了,文人身上不该发出铜臭。 后来我认识的几个朋友在中餐馆老板那里买了蜂胶,是通过关系买的,因为据说一般人拿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买蜂胶,他们说这是巴西特产,临走时我在一家希腊人开的小店里发现了同款,65雷一盒。我问朋友: “中餐馆老板多少钱给你们拿的蜂胶?” “95雷。” 后来我去了一趟巴哈,在那边拍摄几张奥运场馆的建设图,为以后的稿件备用。我和同伴打了一辆车,在海岸线上奔驰,拍完照片已是黄昏,我们返回里约市内,司机一边用单手开车,一边用另一只手在pad上比划。他比划了很久,将pad递给我们,上面是明显用翻译软件翻出的英文: 我十分开心能有这份工作(应该是指我们这单活),让我挣到很多钱,谢谢你们,来自外国的朋友。祝你们好运。 我把pad还给司机,用仅有的葡萄牙语词汇表达谢意,黑人小哥回眸一笑,如沐春风。 临走前,我登上了基督山,几乎所有人都会在耶稣基督像下面张开双臂,像他老人家一样显示出对世人的慈悲,我也不能免俗。但这里游客实在太多,我的同伴几乎躺倒在地上,才能抓拍到一张我身边没人的照片,我怕有人把他的头踩爆,草草脱离了耶稣的怀抱。然后我拍了一张游人远眺里约海景的照片,很像市桥织江在某本杂志封面上的作品,我把它当做这篇文章的头图,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也是个自由摄影师,这似乎该成为我未来的工作。 如今我已经离开里约两年了,换了一份工作,经常为策划苦恼,琢磨着怎么才能在秋季逃出去几天看濑户内艺术祭,拍一两张让我感觉不错的照片。最近里约办了奥运会,网上经常会有关于那里治安糟糕的报道,不知为何,每到此时,我率先想起的是那位黑人司机的笑脸。 -fin- omake 最后分享一些巴西人餐桌上的定番料理 豆饭/feijoada/フェイジョアーダ 黑豆与猪肉、内脏的炖煮,配上饭食用。有些人吃不惯,作为一个米饭爱好者,自然不能放过。 烤肉拼盘/churrasco/シュラスコ 猪肉、牛肉、鸡肉加上岩盐穿刺烤制,放在一起的国民料理。 芝士圆面包/paodequeijo/ボンデケージョ paodequeijo在葡萄牙语中是“芝士面包”的意思,这是巴西人佐餐的主要主食,一般也用来当作餐前面包。 乡下姑娘/caipirinha/カイピリーニャ 以一种名为喀秋莎的蒸馏酒调配的鸡尾酒,加入大量的莱姆和砂糖,是真的很大量,在小酒馆常见。 周磊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suoe.com/llwh/9348.html
- 上一篇文章: 5月5日三分钟新闻晚餐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