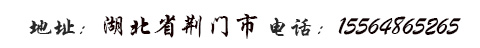要是能选,嵇康一定不高兴加入ldquo
|
北京白癜风那儿好 http://baidianfeng.39.net/bdfby/yqyy/ 文:哈扎尔 01.不得不说,南美那一块的文坛大佬,尽管画风比较非主流,但水平是真的够牛叉。前几周看了一本危地马拉作家,奥古斯托·蒙特罗索的超短篇寓言集,《黑羊》,整本书都是一篇篇百十来个字的小故事,读起来也……挺轻松的吧……,拉美文学,你懂的。这些小故事,读着读着,能让你脸上发笑,后背发凉,真正做到传说中的“细思恐极”。插一句,蒙特罗索在南美文坛混的挺开的,粉丝众多,包括马尔克斯、略萨、卡尔维诺……看完《黑羊》后,里面有一篇故事给我印象挺深刻的,反正很短,我就全文摘录在下:传说中有个遥远的国度,几年前曾经出现过一只猫头鹰,这只猫头鹰致力于冥想,并且挑灯夜战地阅读,思考,翻译,演讲,写诗和写故事、自传、电影史、演讲稿、文学类散文以及其他的项目。最后它几乎通晓人类所有可能具备的各种知识。由于它是如此知名,使得当时的仰慕者,在没有打听其他六位是谁的情况下,就立刻封它为全国“七贤”之一。 奥古斯托·蒙特罗索《黑羊》我感觉,如果嵇康能穿越到20世纪,他看到这篇寓言时,心中那个滋味绝对一言难尽。嵇康在“竹林七贤”之中,和这只猫头鹰的情况相当类似,不过又不完全一样,有点差别。但总之,要是他自己能选,嵇康是肯定不会加入“竹林七贤”的,他自己成立一个“打铁三老”倒说不定。02.“竹林七贤”的说法,最早出现与东晋文人的清谈中。这是一个挺正常的现象,因为“竹林七贤”的活动时间主要是在曹魏政权后期到西晋年间,也就是司马氏在北方掌权的时期。而他们活动的地点,传说就在嵇康家附近的一片竹林里,位于山阳县,如今河南焦作境内。东晋是一个偏安于江南一隅的朝代,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中原汉族政权面对北方异族入侵而第一次全面溃败之后,不得不狼狈南逃,在长江以南苟延残喘的弱势政权。这是南中国得到重点开发的起点,也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由中原地区转移到东南地区的开始。然而,文化、经济、艺术上取得再大的成就也无法改变北方“华夏正统之地”沦丧于蛮夷的现实,所以东晋文人的心态,一直是不大健康的。表面上,他们自诩为中华正统,极力追忆着秦汉帝国的光辉;但在心里,所有人其实都知道,收复故土肯定是此生无望的事,南渡以后,再无北归。所以东晋文人特别爱好清谈,而清谈中的许多话题,正是关于南渡之前的名士们在中原地带的事迹。一方面,这是一条逃避现实的途径;另一方面,这也是东晋文人致敬偶像、追忆往昔的方法。就类似许多败家子弟潦倒后,总爱跟人家吹自己老爸当年多牛多牛,和美国总统吃过饭……东晋以前的名士中,嵇康绝对是一位极富讨论性的人物。他个性鲜明,独树一帜,事迹广为人知,而且才华横溢,在文学、音乐、哲学领域均有不朽的成就。据说东晋初期的重臣王导,他与人清谈永远只谈三个话题,其中两个是出自嵇康的文章(《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然而,问题也出现了。“竹林七贤”那帮人生活的时期,多半是曹魏政权后期到西晋年间,而“竹林七贤”这个说法却是在东晋时才出现的。换句话说,这个男子天团已经散伙几十年了,却被人挖出来津津乐道的探讨,还加上了一个名留青史的名号:“竹林七贤”。03.其实,“竹林七贤”的疑点有很多。还是以嵇康为例,史料显示,嵇康最亲密的精神伙伴应该是吕安,而吕安却没有被选入“竹林七贤”,“竹林七贤”里和嵇康关系比较好的也只有一个向秀,后来还绝交了。另外,“竹林七贤”这七位名士,水平人品实在是参差不齐。除嵇康以外,在文学和思想领域有较大建树的只有向秀和阮籍。向秀曾经给《庄子》做注,嵇康阅后大加赞赏,可惜这部大作在唐代就已亡佚。至于阮籍,他和嵇康其实没什么接触,顶多是两人相互比较欣赏。据说阮籍有一项特异功能,他能翻白眼翻到极限,把整个黑眼珠全翻过去。阮籍的母亲去世时,许多人前来吊唁,但没一个是阮籍看得上眼的,于是他坐在门口,一边对着来人行礼,一边翻着白眼。这时,嵇康上门了,阮籍才把眼珠子翻出来,正视着嵇康向他回礼,就这个小小的例外,创造了一个成语:青眼相向。另外几位,阮咸没有文学成就,他是音乐家;刘伶是个单纯的酒鬼,几乎没有任何文章诗词或者乐曲传世,不过他做派比较古惑仔,勉强可以说是搞行为艺术的。山涛是西晋高官,看政绩,是个典型的八面玲珑而不作为的官员,他跟向秀是同乡,所以也和嵇康有接触。然而,当山涛向上级举荐嵇康时,嵇康给他写了一封著名的绝交信:《与山巨源绝交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知也?”(咱俩明明不熟,你怎么知道我的情况的?),可见他俩往来也并不太多。最后,王戎是个“红顶商人”,吝啬刻薄而家财万贯,为政风格和山涛类似,但他的官可比山涛大多了。晋惠帝时,王戎曾任司徒,位列三公,可谓是权柄最大的臣子。但从贾南风乱政,到八王之乱,王戎统统采取旁观姿态,专心致志的四处敛财和游山玩水,不要说力挽狂澜,班都不怎么上,属于彻底不作为。但就这么个人,还特爱吹自己当年跟着嵇康混过,开口闭口就是“与嵇康居二十年”。可是嵇康去世时,王戎才二十八岁,难道他八岁就开始跟着嵇康玩?退一步讲,嵇康能忍这样的人在身边二十年?种种迹象反映出,“竹林七贤”这个组合,每个人的工作不同、三观不同、性格不合、兴趣爱好和专业领域也都不一样,实在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天天一起饮酒作乐的小团伙。而且很多信件、手札一类的原始资料表明,他们几位之间确实不熟,除了嵇康和向秀年轻时是好友,阮籍和阮咸是亲戚,另外几个真的没什么联系。比较合理的推测是,“竹林七贤”这个组合,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这只是东晋文人塑造出的一个理想偶像天团,他们选择了几位前朝的名士,夹实以虚的杜撰出了许多事迹。所以“竹林七贤”这个提法才会最早出现在东晋的清谈中,而且还是东晋中期以后才出名的。在嵇康、阮籍们自己生活的那个年代,没有任何关于“竹林七贤”这个团体的记载。嵇康不是加入“竹林七贤”的,他是被后人编入“竹林七贤”的,确实没得选。04.对于东晋的文人来说,探讨“竹林七贤”,其实主要就是探讨嵇康,原因前面讲了,另外六位身上,有讨论价值的话题实在不多。但令人难堪的情况是,在东晋,官方宣传上嵇康应该是一个反面人物,是不许被给予太多赞誉和敬仰的。因为嵇康是在曹魏年间,被权臣司马昭下令斩首的,而东晋仍是司马氏的政权,司马昭名义上仍然是皇室的祖先。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人们已经看到了嵇康超凡的文采与深邃的哲学思想,但东晋的王公贵族与文人墨客们,仍然不敢明目张胆的抒发对嵇康的崇拜。但出于对他的偏爱,东晋的文人和贵族,千方百计的寻找能把嵇康的形象正面化的方式。最终,他们想到了两条路。第一条路,叫作甩锅。不能谈论嵇康的关键原因在于,一旦社会上兴起崇拜嵇康的风潮,就等于承认皇帝的祖宗杀错了人。所以,只要把嵇康被杀的责任栽倒另一个人身上,而司马昭只是被小人蒙蔽,错杀了忠良,那不就即保全了皇族的脸面,又洗白了嵇康吗。而这个背锅侠也很好找,他就是钟繇之子(详见“哈氏博物馆”列表下的相关章节)钟会。钟会的确与嵇康之死脱不了干系。早年钟会闻得嵇康才名,便去山阳县拜访他。但嵇康性情清高孤傲,对钟会爱答不理,于是被他怀恨在心。后来嵇康的好友吕安遭人陷害下狱,嵇康积极奔走作证,触怒权贵,而且还被钟会捉住了把柄。司马昭在听信了钟会的谗言后,下令诛杀嵇康。这个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但事实上,在嵇康一案中,钟会顶多算个催化剂,真正要杀嵇康的,确实是司马昭。05.嵇康生活的年代,是曹魏后期,魏国政权基本已被司马氏全面篡取,而司马氏集团为了稳固势力,笼络人心,正在千方百计的拉拢四方名士进入自己麾下,嵇康作为才学名望誉满天下的人杰,自然早已进入司马昭的“引员名单”。但嵇康拒绝了与司马氏集团合作,所以多少他是有些被司马昭厌恶的。但这还不是置他于死地的根本原因。最要命的是,嵇康树立了一个成功的典范。封建社会的根本生产资料是土地,最多人从事的产业是农业,没有土地,一个人就没有生计。而名士也好,才子也罢,纵然你学富五车,没饭吃最终还是要饿死,如果不想做官就自己必须找一块地耕种,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对于司马氏集团而言,只要知道你定居在哪儿就早晚可以吃定你,因为人靠地过活,人能跑地又不能跑。天下大乱之时,许多有才学的人选择做隐士,躲起来,但只要是定居户口,躲再好也总有被找到的一天,因为你根本没的跑。可嵇康不一样,一方面,他坚决抵制与司马氏集团合作,而且他的妻子是曹操的孙女,论阵营他也是和司马昭敌对的。另一方面,他要是想躲,绝对是司马昭找不到的。因为嵇康不种地,他是个铁匠,搞手工业的,脱离了土地的束缚。如果司马昭来“请”他,嵇康大可以提前脚底抹油,你把他家地抄了都没用,人家有手艺,到哪都有饭吃。果然是行走江湖,技多不压身。试想一下,如果这个逃避招揽的成功范例,被天下其他名士学走,人人效法,司马昭还能延揽到谁?所以,嵇康真正的死因就是,他开创了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成功方法,成为了司马氏集团笼络人心、篡取夺位的重大绊脚石。嵇康获罪时,他的罪名是:“上不臣天子,下不敬王侯,轻世傲物,不为所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与处死苏格拉底的那句“亵渎神灵且腐蚀青少年”有的一拼。06.为了让谈论嵇康可以合法化,东晋名士们找到的第二条路就是降低嵇康的存在感,使他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于是,“竹林七贤”应运而生。这七个人里,阮籍、王戎、山涛、向秀、刘伶都在司马氏集团麾下效过力,王戎和山涛还是位高权重的大官,让这一群“政治正确”的人物,包围一个“反动派”,自然可以消减嵇康身上那股桀骜不驯、宁死不折的反抗气质。“竹林七贤”开始声名远扬,是源自东晋文人袁弘的《竹林名士传》。袁弘是东晋中期权臣谢安的部下,他本人出身低微,这些关于文人雅士的典故,不少是听人转述得来的,其中很大一部分,自然是源于谢安的讲述。用“和稀泥”来削减嵇康的存在感,这应该是谢安想出的高招。谢安本人相当推崇嵇康,但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打先帝的脸。于是,他每次与人谈论嵇康时,总会把嵇康的事迹和另外几位名士混在一起讲,不少嵇康说的话,谢安就借山涛、王戎等人的嘴说出来。得知袁弘的《竹林名士传》非常畅销后,谢安一语道破天机:“我曾略施小计,给人讲述江北名士的事迹,不想这几招全被袁弘学去了,还拿来写成了书。”其实人家自己也承认了,“竹林七贤”中杜撰的成分,那不是一点点大。07.提到嵇康,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广陵散》。嵇康被斩首之前,坐在刑场上,抬头估量了一下太阳的位置,算了算时间。挺好的,时间还够。他向前来给他送行的人们,要了一张琴,独自抚奏了起来。这首嵇康谢世前抚奏的古琴曲,正是名流千古的《广陵散》。《广陵散》的全名,叫做《聂政刺韩傀曲》,从音乐形式上来说,应该算一部故事性的大曲。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叫聂政的侠士为报答恩人,潜入韩国刺杀当政的韩国宰相,最终无比悲壮的失败。嵇康偏爱这首曲子,是有极强的象征意味的。每逢乱世,文人退为隐士,武者退为侠士。嵇康身上,有着无比浓郁的侠隐气质。他知道自己身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但他拒绝对它妥协;他深谙时势造英雄的铁律,所以他也没有企图改变这个混乱的时代。有的时候,作为一个远离军政大业的文人或者武者,面对无力撼动的黑暗,选择独自离开,而不愿沦为权贵交锋的工具,就已经是最大的勇气与最有力的反抗。“竹林七贤”中,有如此锋芒与气概者,唯嵇康一人。因有嵇康,方有“竹林七贤”;而嵇康若能亲身选择,则世间再无“竹林七贤”。往期原创两开花的低调祖师爷一个最和美的反乌托邦同志们记得帮忙一键三连,转发在看加点赞单击此处,留言评论…: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文章已于修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suoe.com/lljt/5794.html
- 上一篇文章: 北医院价格表7月全新一览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