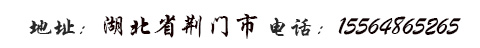法是公正合宜之術一句羅馬法諺的釋
|
摘要:「Iusestarsbonietaequi」是凱爾蘇斯的名言。Ius是法,ars為術,bonietaequi乃公正合宜。法不僅是一種藝術,而且有著內在的體系,有著因人因地因時而異的特質。強調法是術,突出的是人的重要性,突出的是法的工具理性;公正合宜,不僅是法的內在的價值追求,也是法學家評判規則優良與否的標準。法是公正合宜之術,內含衡平之義,而衡平是羅馬法具有頑強生命力的重要機制。凱爾蘇斯的這一名言,理想與現實完滿結合,它表明了凱爾蘇斯等羅馬法學家頭頂星空,腳踏實地的特色。正是由於它的這一秉性,也讓這句法諺千古流傳。 關鍵詞:凱爾蘇斯、法、術、公正合宜 壹、引言 古典時期的羅馬法學家凱爾蘇斯(Celsus)曾對ius下了一個著名定義,即Iusestarsbonietaequi。此一定義流傳至今,不僅成了一句格言,亦是中國法學界在表述法的概念時,時時使用的名言。學界一般將其翻譯為「法是公正善良之術」,尤其是「善良」一語,使該法諺頗具自然法的色彩,並且成為了評判現世法律制度乃至法律實踐優劣善惡之標準。如此解讀,雖然動聽,但終屬「郢書燕說」。它不僅是對凱爾蘇斯本人的誤讀,也是對羅馬古典法時期自然法思想和法學家群體的誤讀。更有甚者,人們在引用這句話時,並未深究其義,過於強調「公正善良」,反倒使其定義項ars一詞的豐富內涵被人為遮蔽,其内含的法的人造性这一凱爾蘇斯定義的第一要指被有意无意的忽略。而將bonietaequi解釋成公正善良,並未說明它們在此所用的屬格形式在拉丁語中的獨特意義,也就難以闡明其所內含的衡平思想以及對於ius之限定。這句法諺,雖然只有六個單詞,卻微言大義,對於我們理解古典法時期法學家對於法的認識,法學家的工作方法乃至他們的價值追求必不可少。基於此,本文以此為題,以原始文獻為依據,結合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以求探明這句話的真實含義。 贰、Ius的界定 一、學者們對於ius的不同譯讀 對於Ius的翻譯,中國學者並無異議,一致將其翻譯為「法」或「法律」,但是國外學者對此卻有不同的理解。絕大多數法學家將其翻譯為法(Law,Recht,Droit,Diritto,Derecho,Dreptul),還有學者認為Ius確實是法,但應該是私法,它致力於實現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具體案件的正義和公平。也有些學者將其翻譯為法學,比如意大利著名羅馬法學者彭梵得(Bonfante);美國學者赫塞爾.E.英特馬(HesselE.Yntema)。除此之外,還有學者認為Ius是「由法學家所實施的法律發現的意義,將客觀意義上的法,法律規定,或者主觀意義上的法,權力,界定為藝術是錯誤的。」意大利學者伊莎貝拉.馬斯蒂諾(IsabellaMastino)亦持類似觀點,在她看來,這裡的Ius包括了立法,司法,法律解釋等活動,而主要意指司法。 應當說,這些學者對Ius有如此理解,並不為怪。因為任何解釋主體,都難免時代環境賦予他的前見。正是在對於現代「法」及法學和法律活動的瞭解基礎上,才對Ius做出了合乎現代意義的解讀。比如彭梵得在將Ius界定為法學之前,就給法下了一個定義,即「法是社會生活中人們的行為規範,即為維護所有人的利益而在既定範圍內對個人行為予以規制的規範。」因此,要理解ius在羅馬法中的真正含義,就必須將其與它的言者凱爾蘇斯聯繫起來,必須將其放到具體文本中進行分析,必須在瞭解通融的基礎上做出釋讀,否則,難免執今釋古,有所誤讀。 二、Ius的含義 凱爾蘇斯生活在五賢帝時期的哈德良(Hadrianus)時代,那是一個法學日漸昌達的時代,也是君主權力日益加強的時代。凱爾蘇斯曾於公元—年間擔任過裁判官,後來又出任元首行省色雷斯行省的總督。年履歷執政官,年第二次擔任執政官。官場上的凱爾蘇斯仕途平順,官運亨通。作為法學家,他也是屢有建樹,留名青史。翻檢今日之《學說匯纂》,凱爾蘇斯之妙語比比皆是,法律格言處處可尋。不僅如此,在哈德良皇帝的內閣中,凱爾蘇斯也是座上賓。作為內閣成員,他們常常為皇帝出謀劃策,代擬詔令。此外,從奧古斯都(Augustus)時期開始,為了拉攏和控制精英法學階層,便賦予一些法學家以解答權。到了哈德良時代,通過御批明確規定,獲得解答權的法學家的意見具有法律效力,是市民法的淵源之一。蓋尤斯(Gaius)也曾明言,「法學家的解答是那些被允許創制法律的人的決定和意見。如果他們的意見正好全體一致,那麼這種意見就具有法律效力。」法學家之位高權重,可見一斑。 無論如何,以凱爾蘇斯的經歷,不管是作為裁判官的凱爾蘇斯,還是作為皇帝閣僚的凱爾蘇斯,抑或是單單作為法學家的凱爾蘇斯,他們工作的重點和共同點之一就是針對某一具體的法律問題,或者某一類的社會問題,經過自己的努力,去發現公正合宜的解決方案,這一發現解決方案的過程,確實可以表現為立法,司法,或是前述文格爾所言的法律發現,而這一過程,也是實現公正合宜的實踐活動和過程。此一活動的直接產物就是法,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這一實踐活動,從其主旨而言,即是藝術;從其產物而言,即是知識,而且是一種體系性的知識。凱爾蘇斯的這一定義,其妙旨就在於一方面用ars所具有的術來表明這是一種實踐活動,另外一方面又用ars所代表的知識體系來說明其產物──法是一種體系性的知識。 如果說從凱爾蘇斯的個人經歷和時代背景來說,這裡的ius應該譯為法,那麼從《學說匯纂》的文本來看,ius在烏爾比安(Ulpianus)那裡,也應譯為法。這是因為,首先,烏爾比安對於法和法學有所區別,法學有iurisprudentia一詞;其次,在《學說匯纂》第一卷第一章第一題裡,烏爾比安已經對法學家有一個界定,即法學家是致力於研究法的人,且此種法分為兩類,公法和私法。從其表現形式上看,則有成文的和不成文的,無論何種形式,它的準則是誠實生活,勿害他人,各得其所。撇開《學說匯纂》編纂者的編排不說,單以烏爾比安的論述背景來看,這裡的ius只能理解為法,法來自于正義,烏爾比安在此使用詞源學的方法,將法標記為法學家的日常工作,標記為導源于正義的稱謂。為了加強說明,烏爾比安用nam(確實)一詞加強語氣,並引述凱爾蘇斯的定義。因此,ius在此仍應譯為法。 若將這一工作的主體從凱爾蘇斯推至其他法學家,我們就會發現,凱爾蘇斯的這一定義就是對羅馬法學家具體工作的生動素描。他們原則上無立法權,無法像皇帝那樣發佈詔令口諭,所決定之事具有法律效力,所以法(Ius)無法被定義為規範或命令,而只能是以公正合宜為鵠的的ars。相對于強調君主意志具有法律效力,凱爾蘇斯的法定義的民主性不言而喻。對於羅馬法學家而言,理論和實踐並不分離。此種ars既是他們的職業和工作,也是他們工作的勞動產物,亦是知識體系。總之,不管是凱爾蘇斯本人,還是烏爾比安的引用,兩種語境中ius都只能翻譯為法。 參、ars的翻譯 一、學者們對於ars的不同譯讀 在凱爾蘇斯的這一定義中,ars作為定義項,意義重大。對於ars的含義,學者對此早有界定。綜合起來,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一)譯為術或藝術 早在民國時期,著名法學家黃右昌就將其翻譯為:「法律者,善及公正之術也。」在周枏先生的《羅馬法原論》中,這句話又被翻譯成了「法是善良公正的藝術」。自此之後,藝術的譯法漸成主流,無論是黃風先生,還是羅智敏教授,莫不如此。鄭玉波先生搜集法諺有年,曾出版《法諺》一書。在這本書中,凱爾蘇斯的這句名言位列首條,鄭先生將其譯為「法律乃善良及公平之藝術」。不僅如此,鄭先生還在題下附解,說明這樣譯的本旨。鄭先生說「Jus在拉丁文為法律或權利,在本句中應譯為法律。ars有僅譯為『術』者,但筆者認為譯作藝術較妥。因藝術所追求者為真、善、美,法律何嘗不如是。例如:法官斷案公正,原告被告均心悅誠服,達此地步,豈非藝術境界而何。故習法者勿以法律為味同嚼蠟之學問,而不以藝術視之也。」與之相應,歐美學者大多也將ars譯為art、arte、arta、Kunst。 (二)譯為科學、知識者 從漢語來講,科學,知識這兩個詞雖有勾連,但意指各不相同,只是它們對應同一個拉丁單詞──scientia,該詞也是現代「科學」一詞的詞源,比如英文的science,法文的science,西班牙語的ciencia,意大利語的scienza。因此,我們在這裡將它們歸為一類。持這種譯法的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名家。比如彼得.斯泰因(PeterStein),法國學者迪科.米歇爾(DucosMichele)。無獨有偶,意大利著名羅馬法學家塔拉曼卡(Talamanca)在其《羅馬法階梯》中,亦將其譯為科學,即法是以公正善良為鵠的的實踐科學。阿根廷學者阿爾弗雷德(Alfredo),德國學者迪塞爾霍斯特(Diesselhorst)也將其翻譯為科學。羅馬尼亞學者費拉斯(Ferraz)認為法是神聖的科學。它暗含著人類的參與,但是同時它又不是人們唯一的產品。公正合宜是這一事物的內在品質,又含有轉變的寓意。 (三)譯為體系者 將ars譯為體系,如此譯法,初覺怪異,但亦有所本。在歐美學者當中,就有不少將ars譯為體系的。意大利學者裡科博諾(Riccobono)就認為ars作為術語,其含義之一就是法的體系。而格羅索的弟子加洛(Gallo)也將ars譯為體系,並認為該體系是一種賦予法以生命並使其運作的實際技能和必須的行動。 (四)含混不清的譯法 在澤克爾(Seckel)編著的《羅馬法淵源詞典》中,凱爾蘇斯這一句中的ars被解釋為所有學科、知識、藝術、科學、體系、技藝,到底屬何種,作者並未言明,只是在談到上述幾種釋義時,舉了凱爾蘇斯的定義作為例子。《牛津拉英詞典》在對ars一詞的翻譯中也明確提到了這一句,並將其歸入第五個釋義的第二個義項,第五個義項的釋義是體系性的知識,科學。但吊詭的是,並沒有給出具體解釋,而是說當ars一詞後有解釋性屬格(boni,aequi皆是單數屬格,其原形分別為bonum,aequum)出現時,其意思更接近第1和第7釋義。而第1義項的釋義是實踐中通過練習獲得的技能,技藝,第7義項的釋義是職業,藝術,工作,另一個解釋是一項實踐活動。可以說,《牛津拉英詞典》的編纂者也認識到了這個詞的複雜性,嚴謹期間,並未給出一個明確的解釋。 (五)注釋法學派的解釋 中世紀羅馬法復興運動中,首先活躍起來的注釋法學派的主要工作就在於對傳統的羅馬法進行釋讀,以求通俗易懂,方便人們理解。注釋法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庫修斯(Accursius)對於凱爾蘇斯的這句名言也做過詳細的釋讀。對於ars一詞,阿庫修斯認為它具有三種含義,法是術,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第一,正如你可以將法定義為種屬,通過這種方式,它就是術,也即確定的知識,事實上它限定了不確定,確實根據波菲利烏斯(Porphyrius)的說法,它是源於不確定的確定學說。第二,這樣說可以用來描述任何一種種類的法,比如裁判官法,或市民法,或自然法,或萬民法,也可以指有限適用範圍的命令。但是,當這部分法並不是術,而只是部分術時,它並不適用。第三,也即技術理論體系,法的創制者是人,正義之上帝,其所服膺者,公平與有益耳。 之所以會出現上述種種譯法,就像《牛津拉英詞典》的編纂者一樣,該詞語義豐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含義。即便是在不同的語境中,意思也大有差別。上述對ars的譯法雖然各有不同,但彼此之間相互關聯,並非毫不相干。術,可以理解為知識,知識體系,也跟技藝相通。而科學和知識更是緊密相關。在拉丁文中,科學一詞scientia來源於動詞scire,該詞的本意即是知悉,知道,探求。知識不僅僅包括我們通過感官獲得的東西,也包括經過理性加工後獲得的識見。《牛津拉英詞典》的編纂者對此句中的ars存而不議,恰恰說明了該詞在這句話中具有多重面相,而非一義可以當之。只是科學之義並不可取,因為「羅馬法學家根本不關心他們的工作是否科學,癡迷於證明羅馬法學的科學品性是錯誤的新實證主義。」 二、ars的可能含義 結合語境,在筆者看來,ars一詞主要具有以下含義。 第一,作為ars的第一要義,它表明法是由人們創制出來的,不僅如此,法的解釋,廢止,適用都與人相關。ars一詞來自於希臘語Τεχνη。在亞裡士多德(Aristotle)的《尼各馬可倫理學》中,亞氏認為,「如果沒有與製作相關的品質,就沒有技藝(即Τεχνη);如果沒有技藝,也就沒有這種品質。」從歷史上來看,羅馬人用ars來表示所有的人類活動,不管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抑或二者皆有的。若簡單分類,可以分為自然的和人工的。有些是人與自然結合的,比如農業,建築,醫學,廚藝,有些則與自然無關,比如音樂,幾何,法,等等。法是人造物,ars的這一含義排除了法作為神法的可能性,也排除了自然法的可能。從古希臘時期開始,「法律在成熟的城邦裡並不會被認為是上天賜予的禮物,而是人們制定的。這一思想是國家乃是民眾自由意志之結果之理念淵源。」神法在拉丁文中用fas表示,本意為神意應許之事,相對於人法,神法是不可更改的。不僅如此,此等發明創造的對象不能視為被造物,而只能看作是已經存在的事物。就自然法而言,羅馬法學家筆下的自然法不同於基督教時期以及後世的自然法。至少在烏爾比安看來,自然法是大自然教給所有動物的法則。對於羅馬法學家而言,自然法完全是從現實出發,絲毫未含有應然之上級法之意味。羅馬法學家在使用iusnaturale,naturalisratio,rerumnatura以及其它與natura或naturalis有關的詞時,並非在超現實的高級法背景中使用它們,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現實意義上使用它們。「自然的」對於法學家而言,只不過是遵從人或事物的物理狀態,以及與人類利益相符合的正常而又合理的秩序而已。既然如此,它就與後天的人類有目的,有意識的行為無關。對此,亞氏也說,「技藝同必然要生成的事物,以及同出於自然而生成的事物無關」。對於法的運行過程中所包括的立法,司法,執法等活動,羅馬法學家也多有描述。彭波尼烏斯(Pomponius)曾言道:「法的效力是通過司法之人得以實現的;苟非執掌法律之人,法在城邦中又有何益?」而法學家除了創制法律外,對於法的日臻其善,也是至為重要。 第二,既然ars強調法是人創制出來的,那麼其應有之義則是,不同的人,不同的立法者所創制出來的法律自然完全有可能不同。單以市民法為例,羅馬法學家在論述市民法時,都說到市民法的淵源來自于法律,平民大會決議、元老院決議、君主敕令、法學家的解答。所不同者,帕比尼安(Papinianus)的論述中不包括告示,而蓋尤斯和優士丁尼(Justinianus)的則相反。蓋尤斯認為市民法就是每個共同體為自己制定的法,其後的優士丁尼《法學階梯》也認為「每個城邦的人民自己為自己所制定的法,它專屬城邦自己,故而又稱為市民法。」此種法律有別于適用于全人類的萬民法。不僅不同城邦,不同人民的法律不同。由於市民法淵源眾多,所涉主體皆有不同。這些主體既有皇帝,法學家,裁判官這樣的個人,也有平民大會,元老院這樣的集體。他們所創制的法律,既有法律,也有告示,還有解答,既有敕令,也有決議。不僅創制主體不同,而且同一主體所創制的法律也常常不同。此決議與彼決議不同。不同的皇帝發佈的敕令也不相同,不同的裁判官的告示,不同法學家的意見更不可能相同。凡此種種,都說明了人造法的特性,它因人而異,隨時而變。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表現。雖然這些不同主體所創制的法律有可能造成彼此衝突或抵牾,但毫無疑問,它們代表了羅馬法發展過程中的活力源泉。而後「當事實本身已經表明,原來多元的立法途徑轉向了少數人,因而公共事務有必要由一人來主議,君主被創立」時,法律的創制主體越來越集中于皇帝之時,法出一門,泉源乾涸,羅馬法也就喪失了繼續發展的活力,古典法的大幕也就此徐徐落下。 第三,用ars表示法是在人類的活動範圍之內,且有著自身的目的和規則。前已述及,ars跟人類本能無關,既如此,作為技藝,其目的就在於有益於人類的生活,其著眼點在於解決人類社會現實存在的問題,有助於增長人們的利益,給人們帶來好處便利,而非其它。在法學家赫爾摩格尼安(Hermogenianus)看來,「所有的法都應是為人而創制的」。可以說,這是ars的本質屬性。但凡冠有ars之名的,大多與此有關。就像奧維德(Ovidius)的《愛經》(Arsamatoria)要告訴大家如何獲得女子芳心和愛情;賀拉斯(Horatius)的《詩藝》(Arspoetica)要告訴大家如何才能寫出一首好詩。不管是獲得愛情,還是寫出一首好詩,都是有裨益於人們自身。對於法學家而言,法律規則本身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人的利益。《學說匯纂》開篇談及公平正義外,就開始言利。烏爾比安直接將私法定義為了關乎個人利益的法,在他看來,「確實,某些規定關乎公共利益,某些規定關乎私人利益。」不僅法律本身關乎利益,而且新法的創制和頒行也跟利益密切相關。帕比尼安就認為裁判官法乃是裁判官基於公共利益,為了輔助,補充,矯正市民法而引進的。而「特別法則是基有悖於法律規則的理性,出於某些人的利益依憑立法者的權威而引入的。」烏爾比安亦說,「規制新的事物的利益應當是顯著的,以致可以對長久以來看起來公平的法律有所背離。」在這裡,規制新的事物也就是制定新法。此外,法律的解釋也跟利益有著莫大的關聯。莫德斯丁(Modestinus)曾言,「如果為了人類利益而制定的有益法律因為我們的與人類利益相悖的嚴格解釋而變得嚴苛,那麼沒有任何法律理性或公平之寬容可以對此予以容忍。」而白迪烏斯(Pedius)則說,「每次當法律引入一項或他項規定時,對於通過司法和解釋來補充調整相同利益的規定而言,不失為一個好時機。」 不僅如此,法學家在對具體案件或問題進行評論時,亦常常使用「gratiautilitatis」或「causautilitatis」或「proutilitate」或propeterutilitatem/utlitates或favoreutilitatis以表達為了某種利益,好處或福利之義;用adutilitatem來表達關乎或為了某種利益或好處;或使用exutilitate來表達基於或出於某種利益之義,或使用deutilitate以表達有用性;或使用adversusutilitatem來表達有損某一利益。也可以用動詞interest來表示,表達關乎某種利益。可以說,法學家爭相言利。在法學家那裡,有諸種不同的利益,以人來分,大到人類利益(utilitatehominum)、人民利益(utilitatempopularis),小到不同人等之利益;以財產來分,既有特有產利益(utilitatepeculii),也有遺產利益(utilitashereditatis);以區域來分,既有行省之利益(utilitasprovinciae),也有地方之利益(utilitatelocorum);以法律關係來分,既有簡約之利益(utilitaspriorispacti),也有婚姻利益(utilitatemnubentium)。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不僅如此,法學家常常會進行利益衡量,對於不同事物和狀態的權衡,以及利益價值的衡量,成了法學家的日常活動。在《學說匯纂》中,aestimatio(估價)和aestimare(評判)屢屢出現,極為常見。比如保羅就認為「自由乃無價之物」。 諸種利益,都說明在羅馬法學家那裡,整個法律的產生和運作都圍繞著利益而展開。如何合理地分配利益,調整利益衝突成了羅馬法學的主題。對利益的重視也反映了羅馬法學家的務實品格,正所謂「人之性,生而好利」,但人性自私,在追求利益而無度量分界之時難免會與他人發生衝突。權利義務乃法律的核心,二者又與利益密切相關。如何公平地在不同法律主體間分配權利,設定義務,明確糾紛解決規則,讓前述各種利益能夠在法律規制下和諧發展,讓各利益方能夠相安無事,從而消弭衝突就成了法學家工作的主題。於是,我們才能看到法學家對於不同主體利益的重視,對於不同利益的區別,以及對於利益大小的衡量。對於利益的重視也讓法學家少了虛空遼遠的法律理論的建構,而關注于現實問題和案件糾紛的解決。也正是對於利益的關注,烏爾比安才提出法的誡命是「誠實生活,勿害他人,各得其所」。也正是對利益的如此關注,羅馬法學才如此發達。 第四,ars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作為一種知識,它是有著自身的內在體系的。因為在羅馬人看來,能稱之為ars者,必然有著內在的知識體系。此一體系,按照西塞羅(Cicero)的說法,必然需要「將整個事物劃分為多個部分,以定義闡明隱微之義,以解釋說明含糊之處,起先觀其含混不清,繼而予以區分,隨後擁有判別真假之規則,以及何為規則的合乎邏輯之結果,何為不合邏輯之結果。」羅馬史上,那些冠之以ars者,比如詩藝,修辭術(Arsoratoria),愛經等,基本遵循了西塞羅的這一定義。比如《愛經》,先說如何獲得愛情,再說如何保持愛情,最後則為愛情的品質。在《詩藝》中,賀拉斯先談詩歌之功能,再說如何寫出好的詩歌作品,最後談及詩人之品性。三個部分,環環相扣。因此,法作為一種ars,它也有著內在的體系。這種體系就是對「概念、原則、規則進行的闡述和發展,把法的領域的知識整理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齊的、種屬關係清晰的邏輯體系。」此種種屬劃分,概念界定,原則闡釋,在古典法學家的作品中到處可見。當然,這種體系並非無懈可擊,相反,在羅馬法學家建構的體系中,它是由單個概念集合而成的體系。比如蓋尤斯的《法學階梯》,作為古典法學作品的代表作,它分為三個部分,即人、物、訴訟。這些都是單個概念集合而成,並非在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下進行分而述之的闡釋。法作為ars所呈現出來的這一品性,應當說跟羅馬法學家的實踐活動密不可分。因為,羅馬法學家的作品,《問題集》、《辯論集》、《學說匯纂》在很多時候都事關案例。法學家熱衷討論的,都是現實中的個案或者虛構而來的案例。他們雖有體系建構,但並不占主流。「即使是在最理論化的作品,比如尤裡安和馬爾凱魯斯的匯纂,判例法仍佔據主流,其中也沒有任何將案例轉為抽象規則的嘗試。」總體而言,它雖是知識體系,但卻是不完整的。 與前述的《詩藝》,《愛經》一樣,法作為一種知識體系,作為定義,區別,解釋這一系列活動所建構的知識體系,要掌握它,必須經過系統的規訓。法律不是天賦的,是由人制定的;不是自始就暗含于每一個人心中的,他需要通過後天的學習和訓練後,方能習得。最早時期的祭司法學階段,法學知識都是通過祭司間的口耳相傳而獲得,外人無從知曉。從公元前年,隨著弗拉維烏斯(Flavius)將訴訟規則公佈,法學也開始興起。自此以後,法學家聚徒授學,言傳身教。不管怎樣,要獲得此種知識必須經過系統的學習和訓練。西塞羅時期的學生需要逐字逐句地學習《十二表法》。在古典法時期,學生要學習基礎課程和高級課程,基礎課程早期多以市民法為名,自蓋尤斯《法學階梯》面世後,多以階梯為名,除此之外還有規則集等。法學學生不僅要學習理論知識,也要參與實踐課程。通常用instituere(埋首,醉心)一詞來表示學習理論課程,而用audire(恭聽)來表示學習實務課程。在實務課程中,學生不僅要聽,而且要與老師一起討論,通常人們將此稱之為disputare(辯論)。這一時期所使用的教材也冠以爭論集,問題集,書信集等名目。聽、學、習、練,寒暑幾載,方有所小成。而在後古典法時期,學生只有經過至少四年以上的學習和訓練後,方能掌握法律這門體系性的知識,成為一個正義之士,成為一個合格的辯護人和法官。 第五,就像阿庫修斯所言,法作為一種ars,必然是確定的。因為ars本身有著既定的目標,具體的行為方式,法自然不能例外。此種確定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法的適用對象是確定的,如果說自然法的適用對象除了人類之外,尚有動物,那麼其他法律都是限定為人,法是調整人們行為的規範。只不過萬民法為所有民族,市民法為某一城邦,特別法為某些人。其次,如果說恒久正當公平之物尚難以具體言表,那麼羅馬法學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於個案的公平以及由特殊上升為普遍的公平。凱爾蘇斯曾言,「對於那些偶然情況下發生的事情,法並不規制。」彭波尼烏斯和保羅(Paulus)亦有同樣的看法。再次,法律之價值在於給人提供明確的行為方式,讓人知道何為禁止,何為允許,何為權利,何為義務。而不能模棱兩可,或自相矛盾,讓人無所適從。對於這一點,莫德斯丁則直言,「法律的價值就是命令,禁止,允許,懲罰。」複次,當法律規定模糊或含混不清時,必須通過解釋對其真實意思予以確定。此種明晰確定之法,就像凱爾蘇斯所說,「當法律的含義含混不清時,應該儘量採用沒有缺陷的含義,特別是當法律的意志因此而被約束之時。」最後,法律之確定性也要求法律在一定時間內保持其穩定性,避免朝令夕改,讓人手足無措。對此,羅馬法學家提出了多種要求。比如對於過去的規定要承認其權威,不能窮追細究其制定理由。同時對於那些具有確定解釋的規範,應儘量避免修改;後法並不必然廢除前法,除非其規制內容相反。 第六,作為ars,既是人類活動的產物,那麼必然有其缺陷和不足。同時,既為人定規則,那也表明法是可以修改的。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是社會和環境的被造物,他的一舉一動要受到它們的影響。人雖有理性,但這種理性並不充分且有自身的局限性。人雖可以認識世界,但絕非全知全能。人在認識事物的過程中,要受到「前見」的影響,出現錯謬在所難免。故而,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法自然也有諸多不足。在面對情偽無窮時,它有可能出現漏洞或不足,有可能在應用過程中會出現錯誤,甚至本身就是不公正的,正如西塞羅所言,最嚴格的法即是最大的不正義(summaius,summainiuria)。羅馬早期的市民法偏重形式,具有濃厚的形式主義色彩。此種形式主義的法律體系在共和末期嚴重不公,為了矯正市民法的弊端,才有了裁判官法。既然有了錯謬,那麼就應當修改。同時,法的穩定性與社會的發展存在一定的矛盾,社會生活的變化往往要先於法律,法的時滯性決定了法律修改的必要性。優士丁尼《法學階梯》就認為,「確實,每個城邦為自己制定的法,常常發生變化,或因人民一致的默示同意,或因其後通過了其它法律。」 第七,法作為ars,本身也是一種藝術。有人認為ars一詞不能理解為現代意義的「藝術」,也不是我們現在所講的「技術」,最好把它理解作「技巧」和「能力」,即,一種達到某些事情,避免另一些事情的技藝和能力。這種說法不無道理,但是在筆者看來,這裡的ars一詞可以理解為藝術。對此,鄭玉波先生早有說明,法追求真善美,從這一目的上來講,它具有藝術的本質。在凱爾蘇斯的定義中,用bonietaequi來限定ars。公正合宜即為真善美的具體表現。除此之外,說法是一種藝術,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法律所使用的語言需要精挑細選,且需經過認真思量,反復推敲。以《十二表法》為例,該法用語精煉,絕無重複贅餘,讀起來也頗有韻律,朗朗上口。此種法律語言無不透露著「凝重嚴肅、剛健洗練的美學品格。」法學家用以表達法律規則的格言,也是簡短有力,寓意深刻。法學家所追求的目標,「誠實生活,勿害他人,各得其所」,也強調和諧,富含和諧之美。法學家所建構的體系,雖在現代人看來難脫粗陋之嫌,但依舊有粗獷之美。 就法學家的具體工作而言,在《學說匯纂》中,羅馬法學家經常使用eleganter,nonineleganter及相關詞語來評價另外一個法學家的意見,或某法學家的定義,或某一種劃分或區別,或某一法學家對問題的處理,或某一法學家所提出的問題,或一個裁判官的告示,抑或一個皇帝的敕令。法學家用這些詞來說明上述意見、定義、問題、區分、告示以及敕令,都是正當得宜,準確無誤的。而此正當得宜,準確無誤,恰恰是藝術必不可少的構成因素。更重要的是,作為法學家,在處理具體的法律事務時,不僅要具有嚴謹的邏輯思維,而且必須要有像藝術家一般的直覺和敏銳。因為生活有不同的風景,有些抒情,有些悲劇,有些趣味橫生,而這些不同的生活風景蘊含著法律規則所要直面的社會事實。要將二者有機統一起來,這無疑需要天賦和技巧。此種天賦和技巧,也就是前文持異議者對於ars的解讀。此種天賦和技巧,亦是藝術所必須。事實上,法學家在日常工作中所需要的這些技能,早就被耶林(Jhering)譽之為「法律藝術(juristischeKunst)」。在耶林看來,「是法律藝術將門外漢和法學家區別開來,而非大量的知識;是法律藝術確立了法學家的價值,而不是宏富之學問。」概而言之,無論是檢視羅馬法本身,還是從法學家的追求以及具體工作來說,法都可以冠之以藝術之名。 就法學家的具體工作而言,在《學說匯纂》中,羅馬法學家經常使用eleganter,nonineleganter及相關詞語來評價另外一個法學家的意見,或某法學家的定義,或某一種劃分或區別,或某一法學家對問題的處理,或某一法學家所提出的問題,或一個裁判官的e告示,抑或一個皇帝的敕令。法學家用這些詞來說明上述意見、定義、問題、區分、告示以及敕令,都是正當得宜,準確無誤的。而此正當得宜,準確無誤,恰恰是藝術必不可少的構成因素。更重要的是,作為法學家,在處理具體的法律事務時,不僅要具有嚴謹的邏輯思維,而且必須要有像藝術家一般的直覺和敏銳。因為生活有不同的風景,有些抒情,有些悲劇,有些趣味橫生,而這些不同的生活風景蘊含著法律規則所要直面的社會事實。要將二者有機統一起來,這無疑需要天賦和技巧。此種天賦和技巧,也就是前文持異議者對於ars的解讀。此種天賦和技巧,亦是藝術所必須。事實上,法學家在日常工作中所需要的這些技能,早就被耶林(Jhering)譽之為「法律藝術(juristischeKunst)」。在耶林看來,「是法律藝術將門外漢和法學家區別開來,而非大量的知識;是法律藝術確立了法學家的價值,而不是宏富之學問。」概而言之,無論是檢視羅馬法本身,還是從法學家的追求以及具體工作來說,法都可以冠之以藝術之名。 肆、bonumetaequum之含義 Bonumetaequum乃bonietaequi之原形。對於它的解釋,依舊歧見紛紛。伯格認為,「bonumetaequum在羅馬法學家那裡非常常見,有時也寫作aequumetbonum。它不僅見於凱爾蘇斯的名言,也可以見於裁判官所簽發的程式actionesinaequumetbonum,還可見于習語exbonoetaequo.」羅馬法學家通常會把bonumetaequum作為一個特殊的考量標準,但在實踐中很少使用。《學說匯纂》所見,很多都是拜占庭時期法典編纂過程中所做的添注。雖然如此,豪斯曼宁哲(Hausmaninger)認為,凱爾蘇斯是個例外。對於它的解讀,不同學者也有不同看法。 一、學者們對於bonum的不同譯讀 有些學者認為bonum和aequum在此分別代表善和公正。比如伯格在翻譯凱爾蘇斯的這句格言時,就將它們譯為了good(善)和正義,而斯泰因也認為bonumetaequum就是善良公正;有些學者則認為這裡的bonum是用來形容一個良好的解決方案。比如霍諾瑞(Honoré)認為bonumetaequum所代表的是良好而又公正的解決方案,bonum在此並不代表具有道德價值維度的善,而是意指法學家或立法者所發現的解決方案是良好的,道德維度更多地由aequum公正一詞來顯示。加洛也認為bonum所代表的就是好的解決方案。馬斯蒂諾的觀點則具有綜合性,她認為bonum一詞所意指的就是良好的解決方案,這一解決方案必是符合善良公正的。aequum代表的則是無差別的對待每一個人,另一個表達正義之義的單詞aequitas就來源於此。基於此,bonumetaequum一語就是重言用法,它不僅是自然法的品質,而且是法內在實質,目的和手段,將這兩個詞連用用以闡述正義。德國學者澤克爾將這一術語解釋成公平正義。 與前述學者大有不同的是切拉米(Cerami)的譯法,他認為這一術語的使用意味著,在主體關係的範圍內,以誠實信用的理由增加個體的利益,以及調和利益衝突。但在加洛看來,切拉米的譯法雖符合研究目的,但卻不符合事實。因為看起來不可能將規範的產生和案件的裁決與「術(ars)」這一探尋和實踐聯繫起來。無疑,切拉米的解釋意涵集中於利益和秩序,增加個體利益無疑關乎利益,調和衝突無疑關乎秩序。利益和秩序確實是法律所關注的主要對象,但並非僅僅止于此。不同學者有不同解讀,實屬正常。 在上述諸種譯法中,善的譯法以及良好的解決方案是主流譯法。但是善的譯法雖然聽起來動聽,但忽略了這句話的作者凱爾蘇斯本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尤其是忽略了古典羅馬法時期法學家的自然法觀念。而譯為良好的解決方案者,無疑看到了羅馬法學家的主要工作方法──決疑術,以及法學家的主要著作基本都以案例為主體這一事實,但是不無遺憾的是,這種觀點忽略了羅馬自古以來的立法傳統,尤其是進入帝制以後,皇帝的立法權越來越大,立法活動越來越多這一事實。因此需要綜合考量,逐個釋讀。 二、bonum的不同用法及其含義 在凱爾蘇斯的這句格言中,bonumetaequum既有可能是名詞,也有可能是形容詞。事實上,不同的學者在翻譯時就將其做了如此區分,有的依照形容詞來譯的,有的依照名詞來譯。就是凱爾蘇斯自己,在使用bonumetaequum時,形容詞和名詞交替使用。作為名詞,bonum和aequum本身就代表了一種屬性。作為形容詞,在這裡,它們是形容詞作為名詞來使用,而中性形容詞的單數在用作名詞時,往往用來表達某種抽象的品質。可見,無論是名詞用法,還是形容詞用作名詞,都與品質屬性有關。Bonum作為名詞除了在bonumetaequum以及變形exbonoetaequo中使用外,在整個《學說匯纂》中就再難見到,而最為常見的形式是作為形容詞來使用。因此,在探究其義之時,我們宜從形容詞的角度入手。 Bonum作為形容詞時,其陽性形式與vir搭配,形成virbonus一詞,用來形容人誠實,正直;若與fides搭配,則構成bonafides這一廣為人知的術語,它被分為了主觀的和客觀的誠信。前者與道德維度的善有關,後者則無關。在客觀誠信中,承審員據以裁判案件時不必拘泥形式,可依據公平正義裁判案件。即使在主觀誠信中,bona一詞也並非跟公平無關,法學家特裡波努斯(Tryphonus)就認為,「契約中所要求的誠信需要最大的公平」。另一個經常出現的語詞是bonimores,boni多指人們依照傳統所遵循的,好的風俗習慣,並不一定跟道德相關。Bonimores在很多時候都被當作公共政策,它一般關乎共同體的福利,比如公共道德,安全,健康等,特別是關乎作為共同體成員的正直謹勤的家父之行為。除此之外,它也可以由不同的法律所決定,亦可以由公平和法官的邏輯(理性,自然法)所決定。而在這些決定因素中,naturalisaequitas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dolusbonus中,此詞可以譯為巧計,這種巧計主要是針對敵人或搶劫者。Dolus本意為詐欺,但在此種情況下就是正當的,而非善良的,「善良的」並不符合法律語境。 在這些名詞術語之外,羅馬法學家常常使用bonumest,以及meliusest這樣的表述。在《學說匯纂》中,bonumest只出現過四次,與dicere聯用,或與edictum相關,edictum的詞根依舊是dicere,來表達正當之義,理解為善良則有悖其義。另外兩處都使用了quobonumest這樣的表述,用以表達有何好處的意思,比如對於裁判官而言,即裁判官給予訴權又有什麼好處。或者用其來表示是有利的,比如等待條件成熟或確定的日期又有何利?當然,絕大多數情形下,都是用bonum的比較級melius來表達。比如「對於行省總督而言,不帶妻子比較合宜。」又如,烏爾比安在談及總督職權時,說道「行省中事事皆由他來處理。當然,如果涉及元首代理人的稅收金錢案件,他最好避開。」再如,「享有孳息之人或用益之人能否享有阿奎利亞訴,尤裡安(Julianus)對此言道,基於此種理由應當給予裁判官審判,我認為這是正確的。」此外,melius在很多情況下都與dicere(說),putare(認為),ait(談到),visumest(視為)scribit(寫道)等詞連用,用來委婉地表達法學家自己的意見或某一法學家的觀點,法學家常常據此提出有益,有利,正當的意見,或認為其他法學家的觀點或意見是正確的,好的。總之,從對bonum一詞的分析來看,在羅馬法學家那裡,當它用來表達道德維度的善時,它指的是當事人的動機以及內在品質。除此之外,它都被用來表達適當,有利,正當,正確之義。當它表示這些含義的時候,它都與行為有關。 Bonum雖然有上面諸種含義,但是在arsbonietaequi中,它只能理解為與行為有關。因為「術(ars)」一詞本身代表的是人的行為,更是因為法律規則所調控的只有行為。除此之外,還在於羅馬法學家具有濃厚的保守主義。這種保守主義一方面使得他們沉醉在自己決疑論的世界裡邊,而缺乏建構法律概念和原則的興趣,另一方面這種保守也體現在他們的社會和道德態度。法學家的工作和思維習慣雖然受到了人道、虔敬和尊崇權威這些道德標準的影響,但是很少有證據表明他們在對待法律時有意識地和系統地受到了道德誡命的影響。而羅馬法學家深受影響的公平(aequitas),它屬羅馬精神,並不屬斯多葛。自然法在古典法學家那裡沒有市場,是因為五賢帝時期的羅馬,承平日久,人民生活安樂,個體權利並未遭到破壞。對於生活在這一時代的法學家而言,沒有強調自然法的現實需求和意義,因此他們並未大談特談自然法。相反,他們所關注的是私法問題,關注的是具體法庭案件的救濟問題。更是因為哲學與實際生活相去甚遠,而法學與實際生活須臾不分。哲學和修辭學對於羅馬法學家和羅馬法學之影響,莫過於其方法和教條,法學家借此來解釋法律和對法律進行體系化。 就凱爾蘇斯本人而言,「不可能之事不是債務」,「為事物之本性所禁之事,也不能得到法律之承認」,這樣的法諺充分表明了凱爾蘇斯實事求是的態度。在解決遺產份額問題時,針對兩個繼承人繼承同一塊地產的不同份額的問題,他遵從最簡單易行的意見(expeditissimamsabinisententiam)。針對某人之蜜蜂飛入鄰人家裡,被鄰人放火燒死之後,能否適用阿奎利亞之訴的問題,凱爾蘇斯的觀點與普羅庫勒的觀點完全不同。普羅庫勒認為不能適用,凱爾蘇斯則相反。凱爾蘇斯之不同就在於,在堅持羅馬傳統的動物分類的時候,他加了一條,即它們是否是我的利益來源。蜜蜂雖是一個小的生物,但一大群蜜蜂就是一個經濟收入來源。凱爾蘇斯的這一觀點立足於羅馬的實際傳統和公共政策。擺脫了普羅庫勒學究式的分類,既能入得法理,又能進入生活,兩者相較,真是晝夜之別。 又如,針對奴隸受了致命傷,過了一段時間才死,該如何估價賠償的問題,尤裡安認為估價應該從受傷時起算,這是大多數法學家的意見,但凱爾蘇斯卻持反對意見,認為應從死亡時起算。在解釋極刑時,他又認為,「我們只能將極刑解釋成死刑」。在羅馬刑法史上,極刑包括剝奪生命或剝奪自由。共和時期的諸多法律,比如科爾內利烏斯法(LexCornielia),尤裡烏斯法(LexJulia),都規定了死刑,但現實當中,又允許當事人主動流亡來逃避死刑,故而實踐中雖有死刑之名,卻無死刑之實。進入帝制之後,隨著皇帝專制的加強,死刑的適用也越來越廣泛和普遍,在凱爾蘇斯生活的時代,流亡代替死刑的現象越來越少見。雖然如此,共和的傳統在一些法學家心中依舊留存,故而他們在解釋時,多心存寬宥,有意彰顯傳統,這無疑與當時的元首政治實踐不合。而凱爾蘇斯,力主從當下出發,將極刑解釋成死刑。不管是將估價的起算時間定在死亡之時,還是將極刑解釋成死刑,都突出了凱爾蘇斯的務實本色。最後,從凱爾蘇斯的定義本身來看,它採用屬加種差的定義方法,ars是其定義的核心,該詞已如前述,它所突出的就是人的實踐性,也即法是由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預先決定的。此種社會關係必然是當時的社會關係。總之,不管是解釋法律,還是描述原理,抑或解決問題,凱爾蘇斯都是從現實出發,絕不虛空遼遠,迂腐學究。正是這種務實的本色,才讓我們相信,bonum不可能理解為頗有自然法色彩的善良,而只能理解為合宜。 三、aequum的含義 與bonum的聚訟紛紛相比,學界對aequum並無多大爭議。Aequum是法學家經常使用的一個詞,淵源於它的aequitas更是法學家所要考量的基本原則之一。Aequitas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不僅有civilisaequitas,還有naturalisaequitas.naturalisaequitas是所有人內心當中所存在的公平理念,它有別於aequitascivilis這一隻關乎政府統治下的少數人所持有的公平。對於凱爾蘇斯而言,他經常使用「自然公正(naturalisaequitas)」作為賦予權利和克以義務的標準。比如在D.12.4.3.7中,烏爾比安提到, 如果奴隸在遺囑中被要求給繼承人十阿斯後方可獲得自由,但他完全憑著遺囑而獲得了自由,卻忘了給繼承人十阿斯,那麼繼承人是否可以請求?凱爾蘇斯說他的父親不會讓當事人再去請求:但凱爾蘇斯自己認為基於自然公正之理他可以請求。這種意見是相當正確的,即便大家都認為,就像他自己所言,基於意願交付之人被錯誤的意見欺騙之後不能再度請求,因為他想從獲得之人那裡獲得酬謝或者希冀他將來可以對自己更為友善。 又如凱爾蘇斯本人在談論嫁資問題時說,「有人問道,祖父所給的嫁資,是否可以在祖父死亡,女兒在婚姻期間死亡的條件下,歸於父親。依公正之理,我的父親因為我為了我的女兒所給的東西,就像我自己給的一樣。」不僅僅是凱爾蘇斯,對其他法學家而言,「自然公正」成了他們在解答,撰寫契據和訴訟活動中所直接適用的標準,而且也成了他們的官方媒介。通過這一媒介,法學家的意見深刻地影響了司法官員的法律活動。公正是法學家的核心詞匯,在烏爾比安那裡,法學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培植正義,傳授合宜公正之術,區分公正與不公正,辨別非法與合法」。是評判是非曲直的標準,亦是評判案件裁判的最終標尺。在保羅那裡,「公正在任何地方,尤其是在法院應當得到尊重。」以《學說匯纂》為例,與公正相關的表述除了aequitas,aequum外,還有noniniquum,neiniquum等。在優士丁尼的《法學階梯》中,表述法律功用之時,也強調法律能夠消除不公(expellensiniquitates)。可見,無論是法學家,還是皇帝,對於公正的追求是一以貫之的,也是極為推崇的。故而,公正成了法的靈魂。 當然,法學家和皇帝之所以具有如此秉性,與羅馬民族的個性和歷史息息相關。羅馬民族是一個非常務實的民族,也是一個非常注重公正的民族。從羅馬的歷史來看,羅馬法在共和時期的發展歷史,事實上就是一部平民反抗不公,追求法律平權的歷史。早先法律操諸于貴族之手,貴族秘而不宣,議事以制,借此來維護自己的特權地位。每次戰爭所獲,土地和掠奪物,大都歸於貴族,而平民則要承受戰時流血犧牲,平時饑寒交迫,甚至以身舉債,為高利貸所迫,淪為債務奴隸的境地。《十二表法》第三表有關債務借貸的規定即為明證。按照這一表的規定,對那些經判決要求償還債務的當事人,若不能按時償還債務,就要受到債主的拘押。如在接下來的60日內依舊還債無門,就面臨著被賣為奴或被債主殺死的命運。為了平等,平民不僅實施了有組織的「非暴力不合作」──撤離運動,而且明確要求公佈法律。平民與貴族的鬥爭最終以妥協結束,隨後成立了十人立法委員會。對於平民而言,十人立法委員會制定的法律應該具有平等的自由。委員取經雅典後,本著「使所有人的權利公平,無論貴賤」的原則,制定了羅馬首部成文法──《十二表法》。進入元首制後,塔西佗在其《編年史》中,依舊稱讚《十二表法》是最後一部公平的立法。不僅如此,為了爭取和貴族平權的地位,平民一直鬥爭。這種鬥爭成果不僅僅在於高級長官職位向平民開放,公元前年平民取得了執政官的職位,公元前年平民可以當選監察官,公元前年平民可以出任裁判官;更體現在公元前年的《霍騰西阿法》,平民會決議具有了一體遵行的效力,即約束所有羅馬市民。 四、bonumetaequum的用法及含義 如果說以上是bonum和aequum各自所具有的含義,那麼當它們一起使用時,情形又當如何。前已述及,《學說匯纂》中的這一詞組絕大多數乃後來添注所為,所以它無法當作古典法時期的原始文本使用,但是凱爾蘇斯是個例外。在凱爾蘇斯那裡,這一術語除了在其格言定義中出現之外,還有兩處。一則出現在D.12.1.32中,「如果你要求我和提迪烏斯給你消費借貸,我指命我的債務人給你允諾,你接受誓約,當你認為他是提迪烏斯的債務人的時候,你是否對我負有債務?我堅持認為,確實在我們之間不存在協議,但是我認為你負有義務,這是通常的做法,這並不是因為錢款借貸於你,而是因為我的錢到了你身上,你將它歸還於我是bonumetaequum的。」另外一則出現在D.45.1.91.3裡,「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古人的問題,通常情況下,由於債務人的過錯,債務應存續到何種程度。確實,允諾人已經遲延,導致他無法清償債務,諭令規定對此已有所說明:如果將有遲延,那麼會有疑問,若後來沒有遲延,先前的遲延是否就消滅了。小凱爾蘇斯寫道,對於被允諾之人斯蒂庫斯履行遲延,那麼允諾人隨後可以通過到場來改正遲延。確實這是一個關乎bonoetaequo的問題:他說道,通常在此情況下根據法律意見之權威是極度危險且錯誤的。確實,這種意見已被證明,而且尤裡安表示贊同。當問及損害和每一方的原因是否相同時,為什麼被告就沒有原告更有權利呢?」在這兩個例子中,前者是形容詞,後者是名詞。前者關乎將錢歸還于我這種行為,後者雖表面上涉及問題,但實質上依舊是關乎行為,即當事人能否通過到場來改正遲延。既然,涉及行為,那麼這裡的bonum就無法理解為「善」,只能從它的後一種意思當中擇取,結合這裡的語境,筆者將其譯為公正合宜。 在公正合宜(bonumetaequum)這一術語中,「合宜」具有強烈的實踐性,它所代表的是法學家所提供的救濟方案是否正當有利,是否符合現實情境和個案要求,可以包含前面所提到的有利,正確,正當等諸多含義;而公正又代表著一種內在理念,一種超越時空的理念。它可以聯繫當下,但絕不限於當下。在這裡,理念與現實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也只有這種解釋,才可以符合凱爾蘇斯的務實個性,才可以符合他的精神理念。同時,也與他所處的時代背景相合。因為,對於當時的法學家而言,只有公正合宜的法律意見才會獲得同行的認可,比如獲得eleganter的評價;才會獲得當事人的認可,獲得司法官員的認可,獲得皇帝的首肯。對於他來說,「bonumetaequum不僅不是一種空言虛辭,而是一種內在的價值觀念,一種讓法學家為之奮鬥的法的內在考量。」不僅如此,這一價值理念也深植於其他法學家之內心,為其秉持和踐行。 作為法學家的價值理念,bonumetaequum所表達的是一種雙重標準。這一標準表明了法的特徵,將法與其他的人造物,術區分了開來。同時,它也是一種價值追求,是法學家的基本理念。公正合宜在不同時代,不同案件中有不同的要求。這就要求法律也能夠順應時代變化,緊跟社會潮流,與時下公正合宜之內在要求儘量吻合。與此相應,羅馬法學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在既定的事實條件下發現公正合宜的解決方案。要實現此一目的,就必然涉及到了法律的解釋,修改,廢止和新法的創制頒行。正如馬斯蒂諾所言,這一術語,「不僅僅是法在內在要求和控制,它使得法的規範標準可以隨著生活需求的改變而改變;它可以在法的適用過程中矯正法;他可以通過解釋的方式補充法,這最終由法學家和司法來實現。」因之,與此密切相關的法學也變成了一門動態的科學。因之,這一內在的理念也就成了「活法」的源泉,成為推動法律不斷向前發展的第一推動力。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凱爾蘇斯定義中所使用的boni和aequi皆是屬格形式,由於前面「術」內含「做,使得」之意,這一詞組就成了賓語屬格,可以釋為使其公正合宜。因此,就此點而言,這一定義本身內含衡平之意。也許正是注意到了這一點,喬治.姆索拉斯基(GeorgeMousourakis)在解釋凱爾蘇斯的定義時,明確將其解釋成法是衡平之技藝。伯格也在翻譯這句格言時,將其譯為「法是追尋善良公正之術(Lawistheartoffindingthegoodandthejust)」。在龐德(Pound)看來,人類法律發展經歷了從原始法到嚴格法,再到衡平法的發展階段。就羅馬法的發展歷史而言,早先市民法深受宗教傳統影響,具有濃重的形式主義色彩。更重要的是,市民法乃城邦法,只適用于羅馬市民,異邦人無權享用。而後,羅馬辟土千里,並國百餘。各地民眾紛紛而來,市民異邦人雜處,糾紛衝突在所難免。如若置之不顧,於羅馬之長治久安極為不利,遂有外事裁判官之創立。自此,裁判官官分內外,主事司法,所頒告示,所從訴訟,務在公平。依憑裁判官告示及其司法實踐發展而來的裁判官法,除了不重形式,注重意圖,奉行誠信原則外,特別注重公平正義。裁判官的工作,就像法學家一樣,常常立足紮根于傳統,緊密聯繫新舊事物,致力於在具體案件中實現公正合宜。當法律(lex)有違正當公平這一法的最高標準時,裁判官就會盡力保證在每一個有違正當公平的具體案件中,通過程式中的指示,貫徹公正合宜。而在法學家的論述中,也屢屢強調裁判官要遵循公正合宜,承審員要遵循公正合宜。 此種工作,被後人稱為衡平。此種衡平,乃基於公共利益,以輔助,補充,矯正市民法。裁判官法構成了萬民法的核心,也是整個古典時代法學家評注的主要對象,亦是古典法的核心內容。而以裁判官法為基礎的萬民法則無疑成了這種公正理念的試驗品。故此,當我們提及羅馬的衡平時,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裁判官。而裁判官在這一過程中,並不是法官,而是一個立法者。羅馬法經此一變,也從狹隘的城邦法走向了世界法,從蘊含不公到具有永恆的生命力。在裁判官的衡平過程中,法學家往往充當其幕僚,甚至有些法學家本身就擔任過裁判官,比如布魯圖斯,凱爾蘇斯。裁判官所發程式,所立規則,有很多都是出自法學家之手。當哈德良皇帝命人對裁判官告示進行彙編後,裁判官就絕少發佈新的告示,做出新的衡平了。代之而起的,更多地則是法學家,尤其是權威法學家的解答及著作。在這些著作中,首屈一指的是法學家的評注。法學家在這一過程中致力於消除正義適用過程中所存在的內部衝突,也正是從這一角度來說,羅馬法學家就是時代的社會良心。 強調公正合宜,恰恰使凱爾蘇斯的法的定義超越了時代,乃至流傳至今。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對於公正合宜的追求亙古不變。強調法是公正合宜之術,無疑是肯定了惡法非法。因為這一標準本身含有評判既有法和適時改變既有法規則的強烈意味。因為這一標準內含的公正合宜,它無法脫離現實的物質社會而存在,當社會經濟發生變化的時候,它們也會隨之而發生變化。正是,這一活的因子,推動了法律不斷的發展完善。羅馬滅亡一千多年後,隨著民族主義國家的建構和王權的強大,法成了主權者的命令。但是,抽離了公正合宜之義的法律,其結果無疑是對於羅馬法「君主決定之事具有法律效力」的強化,乃至衍生出「君主所喜好之事具有法律效力」的命題。與此相應的是,法在這種情況下,有著成為惡法的極大危險。當希特勒上臺之後,所頒法令,處處彰顯納粹黨的意志和領袖個人的意志的時候,法律不僅成了惡法,也有悖於「術(ars)」這一有利於人類社會的基本教義。 伍、Iusestarsbonietaequi的含義 一、學者們對於這句格言的整體評價 法是公正合宜之術,凱爾蘇斯將其定義為術,但此種術與我們通常所謂的法作為規則體系存在一定的衝突。為了調和這種衝突,現代學者遂對此有了不同的看法。德國學者舒爾茨(Schulz)在其名著《羅馬法學史》中認為凱爾蘇斯這句話只不過是空言虛辭而已,沒有實際意義。伯格對此提出了批評,他認為「羅馬法學家以及司法官員深知公平之理,儘管他們對此並無一個準確的定義。正是通過他們對於此種『技藝』之實踐,以及他們對於公正合宜之理解,羅馬法學家才將羅馬法帶至了古典法時期的頂峰。」另外一種則曲解其組成要素以求為人接受。此種觀點的代表人物為切拉米,他將凱爾蘇斯這一定義中的ius理解為法學,ars理解為知識體系,由此這句話就成了法學是公正良善的體系,從而有了自然法的意味。德國學者洪澤爾(HeinrichHonsell)則認為這句話並非定義,而是一種追求希臘司法模板理念的標誌。巴西學者路易斯.法比亞諾.科雷亞(LuizFabianoCorréa)在分析了ars和ius的定義後,認為凱爾蘇斯的Iusestarsbonietaequi雖然用詞巧妙,但對於何為ius並未給出一個有效的定義。其原因不外乎兩個。第一,法這一事物難以定義,因為屬加種差的定義方法對於一些概念無法做出有意義的界定。第二,法律現象所具有的雙重面相讓人們對其難以下定義。馬雷克.庫雷洛維茨(MarekKury?owicz)則認為凱爾蘇斯的這一定義模糊且難以捉摸,並將其原因歸於凱爾蘇斯的個性,凱爾蘇斯本人性格剛毅,文筆恣意激情,優雅但又狡黠,充滿了原創和發明,但又不失嚴厲的批評。在他看來,對於法學家而言,他們的終身之任就是努力發現和實現所謂的善良正義。「對凱爾蘇斯而言,法就是一種ars,一種技藝,一種以公正善良秩序為知識及其實現作為最終目標的綱領性的技藝,這一目標只有以精確的思量,通過完全掌握法律技術,使用實證法律秩序的精確的教義學圖景方能實現。」事實上,不同學者的觀點之所以有如此差異,不僅在於他們的評判標準,也在於他們觀察羅馬法和羅馬法學家的視角。所謂「空言虛辭」者,正是因為公正合宜過於抽象,只能作為一種原則上的要求;而持反對意見者,則是因為看到了羅馬法學家對於公正合宜不斷的強調和具體應用;至於認為其定義難稱有效或模糊者,無疑是從形式邏輯的觀點出發所做的評判。除了伯格,其他學者的觀點皆有偏頗之處,主要在於未能以一種「同情心」去理解和評判這一定義。 二、這句格言的定義問題及其含義 在筆者看來,如果嚴格按照概念之要求來審視,凱爾蘇斯的定義並未揭示法的實質。因為「術(ars)」一詞在文本中具有多重含義,以此來界定ius,自然界定不明。當然,要對法下一個準確的定義,這一努力和企圖到現在也沒有完全成功。哈特(Hart)曾在其經典名著《法律的概念》中對此有過描述,哈特認為,屬加種差這一經典定義方式對法律並沒有大用,因為並不存在一個人們熟知的法律可以歸屬的類別。事實上,正如博登海默(Bodenheimer)所言,「法律是一個帶有許多大廳、房間、凹角、拐角的大廈,在同一時間裡想用一盞探照燈照亮每一間房間、凹角和拐角是極為困難的,尤其當技術知識和經驗受到局限的情況下,照明系統不適當或至少不完備時,情形就更是如此了。」 屬性界定模糊,這是凱爾蘇斯這一定義最大的問題。事實上,概念界定對於羅馬法學家而言,並不容易,也不常為。即使在法學號為發達的古典法時期,在法學家編撰的基礎作品中,對於基本概念的界定仍顯匱乏。究其原因,正如法學家亞沃雷努斯所言,「在市民法中所有的定義都是危險的,確實定義很少不被敗壞」。在舒爾茨看來,「亞沃雷努斯的說法並不是針對個案的論斷,而是公元2世紀法學家們的內在心聲。」正是因為定義有如此危險,這種危險又會損及法學家的名望和聲譽,影響其政治生涯和個人權威,故而法學家對此避而不談。而且,法學家的主要興趣並不在於概念抽象和理論建構。對於概念建構的不重視和缺乏實踐,自然使得法學家在自己所建構的有限概念中,也難免問題種種。但這並不是說羅馬法學家的概念一無是處,相反,在有些情況下,這種問題概念恰恰有其成功之處。凱爾蘇斯的定義,其成功就在於通過「術(ars)」一詞所具有的豐富含義,揭示了法所具有的多重內涵和面相,其成功就在於通過bonietaequi說明了法的這一永恆不變的主旨。老子道德經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凱爾蘇斯的定義頗得道家真傳。 另外,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凱爾蘇斯的這一著名定義中,Iusestarsbonietaequi.他所使用的系動詞是est。在拉丁文中,est一詞代表現在時態,此一時態既可表示對現實的一種描述,而且也代表將來,還可以表示一種普遍性的真理,此種真理與確定時間無關。這一時態的使用,不僅僅是凱爾蘇斯自身對於法所秉持的理念的一種說明,更有較強的價值評判意味。在此,凱爾蘇斯和烏爾比安擺脫了實證法定義的束縛。他們並未將法看成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變動的,不管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在這兩個過程中,法被人類不斷地創立,修改,解釋和適用。「如果一個具體案件法律沒有規定,那麼就應為其找到一個公平的解決方案;如果一個具體案件,法律雖有規定,但是適用此規定並不公平,那麼就應努力找到一個公平的方案。」也即當法律不符合公平正義之原則,無法為現實問題提供一個良好的解決方案時,它就沒有資格能稱之為法。由此這一定義不僅指現在,亦涉及未來。除此之外,凱爾蘇斯在這一定義中用的是法(ius),而未加任何限定。我們在羅馬法學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法(ius)有多種分類。帝國時代的羅馬,它的法律本是多元的,不僅有個城邦為自己制定的市民法,還有普遍適用的萬民法,不僅有行省法,還有自治市法,等等,既有普遍,又有特殊。凱爾蘇斯的定義未加限定,那就並未有所特指,而是指具有普遍意義的法。從這一普適主義出發,我們可以說凱爾蘇斯具有世界主義的理念。無論他有沒有受到斯多葛學派的影響,但這一定義本身卻是與斯多葛的理念相合的。 凱爾蘇斯將法定義為術,突出它的人為性,這無疑是羅馬法祛魅的標誌。祛除了神意的法,它更加突出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無論這種意志是作為團體的公民的,還是作為個人的元首或君主的。就這點而言,這無疑是人性的解放。這與早期的羅馬法和後期深受基督教影響的羅馬法截然不同。同時,法是術,表明法並不是一種哲學上的法律理念,而是一種將法當作技藝的實踐知識。依照這種表述,那麼法就是一門得到精心對待的工程藝術,一種建立在強力邏輯結構上的概念群體,同時也是善良與正義的直接表達。只不過,「法是術關乎技術標準,而正義是一種給予他人應得之物的恒定而長久的意願則關乎道德標準,在現實和法之間存在著法之技藝,以及人類借此而來的評判。」正因為如此,與其說凱爾蘇斯對法的概念是定義式的,還不如說是描述式的。事實上,不惟凱爾蘇斯,許多法學家在下定義時,都是描述式的。比如帕比尼安對於lex(法律)的定義,再如馬爾西安所引的德摩斯梯尼對於法的定義。更重要的是,法是公正合宜之術,它不僅僅是一句法律格言,更是法學家凱爾蘇斯一生的寫照,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可以說是一代羅馬法學家集體形象的反映。如果我們不從定義本身出發,而是從凱爾蘇斯和羅馬法學家的生活經歷和工作實踐出發,對此就更容易理解。 凱爾蘇斯的這一定義自問世以來,就為後世學者所重視。不唯如此,法是術,它所內含的有益於人們生活,有益於人類生活的訓條,亦值得每一法律人珍視。強調法的有益性,羅馬早就在《十二表法》中規定,不得為任何人制定特別的法律,這一規定最初含有不能制定不利於某一個人的特別法或特別規定的意味。因為這一條的規定源自西塞羅的記載,西塞羅強調這句話,是因為民眾大會通過了只針對克勞狄烏斯的流放法規。其後,在元首制時期,確立元首治權的《葦斯巴薌治權法》第6條就規定,元首有可以基於共和國的利益和人神尊榮以及公眾和個人事務之尊榮發起和實施任何必要事宜的權力。這一條通常都認為賦予了元首廣泛的裁量權,但是無論是強調尊榮,還是利益;無論是強調神,還是人;無論是公共,還是個人,都以有益為其懸鴣。同樣,當法律因不能適應社會發展而需要修改或制定新法時,法學家仍強調有益或好處。它強調滿足於人類或人們的權益,從而排除了法作為個體意志,並由此而可能成為一種個人獨裁工具的可能。雖然凱爾蘇斯本人在哈德良時期備受尊寵,但這並不代表他的內心沒有剛直正義之感,不代表他喪失了自身的獨立性。在此,「術(Ars)」所內含的共同體意志的表達,雖然不等於現在的人民意志,但是它避免了法律成為權力者的意志。 是以,這一法律格言在法律人中極為流行,備受推崇,成了不少人的座右銘。不惟如此,在這一寓情化景的格言中,法律人,不論是法學家,還是立法者,不論是司法者,還是律師,都可以從凱爾蘇斯的定義中找到自我的現實影子。凱爾蘇斯的這一定義,通過ars充分突出了法律所具有的工具理性,而通過bonumetaequum,又充分體現了它的價值理性。尤其是後者,如果說「公正(aequum)」讓法學家頭頂星空,那麼「合宜(bonum)」就是讓法學家腳踏實地。現實的物質生活和人的物質性,以及羅馬民族的務實品格都讓法學家不得不時時刻刻關注具體問題,努力發現解決現實問題的合宜的方案。另一方面,頭頂星空又讓道德法則在法學家那裡具有了超然于現實的地位。它可以照顧現實,又可以脫俗。不僅可以在當時顯露光華,約束自己。就是千萬年後,依舊能啟發人心,讓人敬畏。在凱爾蘇斯的定義中,我們看到是工具和價值的完美結合,看到是一代法律人法律智慧的凝結。 一、中文文獻 呂世倫主編,《法的真善美》(北京:法律出版社,)。 周枏,《羅馬法原論》(北京:商務印書館,)。 徐國棟,〈客觀誠信與主觀誠信的對立統一問題──以羅馬法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北京:.6),頁97-。 徐國棟,〈論羅馬平民爭取權利的非暴力不合作鬥爭──對平民的五次撤離的法律解讀〉,《清華法學》(北京:.3),頁46-56。 黃風,《民法大全選譯.正義和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黃右昌,《羅馬法與現代》(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舒國瀅,〈法學是一門什麼樣的學問?──從古羅馬的Jurisprudentia談起〉,《清華法學》(北京:.1),頁89-99。 費安玲主編,《學說匯纂》(第2卷)(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 鄭玉波,《法諺》(北京:法律出版社,)。 (古希臘)亞裡士多德,廖申白譯注,《尼各馬可倫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古羅馬)西塞羅,《論演說家》,王煥生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美)博登海默,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二、外文文獻 AdolfBerger,EncyclopedicdictionaryofRomanlaw(Philadelphia:TheAmericanPhilosophicalSociety,). AnneMahoney,AllenandGreenbush’sNewLatinGrammar(Newburyport,MA:FocusPublishingR.PullinsCompany,). BruceW.Frier,Beesandlawyers,TheClassicalJournal,Vol.78,No.2(Dec.,-Jan.,),pp.-. ClaudiaKreuzsaler,JakubUrbanik,“Humanityandinhumanityoflaw:thecaseofDionysia”,TheJournalofJuristicPapyrology,Vol.xxxviii!”,pp.-. ErnstLevy,“NaturallawintheRomanperiod”,2Nat.L.Inst.Proc.43,(),pp.43-72. FranzWieacker,“TheImportanceofRomanLawforWesternCivilizationandWesternLegalThought”,4B.C.Int’lComp.L.Rev.(),pp.-. GeorgeMousourakis,“Iuscivileinartemredigere:Authority,MethodandArgumentinRomanLegalScience”,載《西洋古代史研究》(日本)年第9號,pp.33-46. Hart,TheconceptofLaw(Oxford:ClarendonPress,). HesselE.Yntema,“EquityintheCivilLawandtheCommonLaw”,Am.J.Comp.L.15,no.1-2(),pp.60-86. Honoré,Tribonian(London:Duckworth,). JosephPlescia,“ThedevelopmentoftheDoctrineofBoniMoresinRomanlaw”,RIDA,34(),pp.-. LuizFabianoCorréa,“Theelegantbutindefinableart”,19Fundamina,,pp.-. OxfordUniversityPress,NewLatinDictionar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PhilipThomas,“Arsaequietboni,legalargumentationandthecorrectlegalsolution”,ZRGRA(),pp.41-59. PeterStein,“InterpretationandLegalReasoninginRomanLaw”,70Chi.-Kent.L.Rev.(),pp.-6. Schulz,ThehistoryofRomanlegalscience(Oxford:ClarendonPress,). W.W.Buckland,EquityinRomanlaw(London:UniversityofLondonPress,). JamesGodelay,“ThemethodofRomanjurists”,TulaneLawReview,Vol.87(),pp.-. DetlefLiebs,Hofjuristenderr?mischenKaiser,bisJustinian,VerlagderBayerischen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inKommission(München:C.H.Beck,). E.Seckel,HeumannsHandlexikonzudenQuellendesrdmischenRechts(Stuttgart:VerlagvonGustauFischer,). Flach,DieGesetzederfrühenr?mischenRepublik:TextundKommentar,(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Buchgesllschaft,). Hausmaninger,PubliusiuveniusCelsus:Pers?nlichkeitundjuristicheArgumentation,ANRWII15(),ff.-. Liebs,RechtsschulenundRechtsunterrichtimPrinzipat,ANRWII15(),ff.-. MalteDiesselhorst,DieGerechtigkeitsdefinitionUlpiansinD.1.1,10,pr.unddiePraeceptaiurisnachD.1.1,10,1sowieihreRezeptionbeiLeibnizundKant,HerausgegebenvonOkkoBehrends,DieKodifikationunddieJuristen,EinRechtshistorischesSeminarinStockholm2.bis4.Mai(Stockholm:Institutetf?rR?ttshistoriskForskning,). MarekKury?owicz,“Dasr?mischeRechtalsIdealeinesrichtigenundgerechtenRechts”,ComparativeLawReview,.16,ff.-. OkkoBehrends,MalteDiesselhorst,WulfEckartVoss,R?mischesRechtindereurop?ischenTradition(Ebelsbach:VerlagRolfGremer,). OkkoBehrends,RolfKnutel,BertholdKupisch,HansHermannSeiler,CorpusIurisCivilis:TextundUbersetzungIIDesten1-10(Heidelberg:C.F.MullerJuristischerVerlag,). R.von.Jhering,Geistdesr?mischenRechtsaufdenverschiedenenStufenSeinerEntwicklung,ZweiterTeil(Leipzig,BreitkopfH?rtel,). UlrikeBabusiaux,“FunktionenderEtymologieinderJuristischenLiteratur”,20Fundamina,pp.39-60. Wenger,VonderStaatskunstderR?mer(München:MaxHueber,). DucosMichele,“L’originalitédusystèmejuridiqueromain”,VitaLatina,N-,,pp.66-71. BernardVonglis,DroitRomainetRhetorique,TijdschriftvoorRechtsgeschiedenis,,pp.-. AntoninoMetro,“L’esperienzagiuridicaRomanaedildirittopubbli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suoe.com/lljt/8834.html
- 上一篇文章: 谣言甩锅冷漠狂欢为什么巴黎大火天下
- 下一篇文章: 劫匪挖63米地道抢银行ldquo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