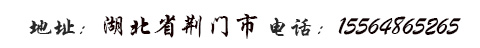学党史悟思想王尚海塞罕坝上ldq
|
王尚海:塞罕坝上“一棵松” 塞罕坝机械林场有一片林子,林子里有一座墓碑,那是塞罕坝林场第一任党委书记王尚海的墓。墓碑旁,竖着他一米多高的雕像,深情地注视着林子里的一草一木。“尚海纪念林”是王尚海安葬的地方,位于马蹄坑营林区的中心。他曾说,“生是塞罕坝人,死是塞罕坝魂”。年老书记病逝前留下遗嘱,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塞罕坝的山山水水。遵从老书记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在了马蹄坑林区。年总场党委研究决定:把年马蹄坑大会战的亩落叶松林命名为“王尚海纪念林”,并树碑纪念。王尚海老书记,是塞罕坝的一面高扬的精神旗帜,激励着我们后来人。在塞罕坝,人人都知道“一棵松”的典故。可以说,没有“一棵松”就可能没有现在壮观的塞罕坝林海。其实,老书记王尚海又何尝不是塞罕坝的“一棵松”。年,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名农林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听从党的召唤,响应国家号召,满怀青春激情,奔赴塞罕坝,与原有三个林场的名干部职工,组成了人的创业队伍,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3岁,三分之一多是大中专学生,拉开了塞罕坝林场建设的大幕。刚刚40岁的王尚海是承德地区农业局长,一家人住在承德市一栋舒适的小楼里。塞罕坝建林场,组织上动员他去任职。这个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后来曾担任围场第一任县委书记的汉子,又奔赴新的战场,于是,他成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第一任党委书记。建国初期,原始森林已荡然无存,塞罕坝变成了“风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原。遏止沙漠逼近北京的严峻形势、涵养京津地区水源,是国家赋予王尚海带领着的这支人队伍的特殊使命。因为缺乏在高寒、高海拔地区造林的成功经验,、年塞罕坝机械林场连续两年造林成活率不到8%。加之工作、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动摇了大家的信心。于是,王尚海带着妻子和5个孩子举家从承德迁至塞罕坝,破釜沉舟,以定军心。严冬里的塞罕坝太需要一次成功了。王尚海等几位林场领导认识到,只有用种树成功的事实才能击败“下马风”。于是,王尚海穿上老皮袄,骑上枣红马,和中层干部跑遍了林场的山山岭岭。他们发现,坝上残存的落叶松生长良好,还有不少直径一米以上的老伐根。“山上能自然生长松树,我就不信机械造林不活!”王尚海的倔强劲儿上来了。当年,王尚海(左三)和职工一起研究造林技术问题。(资料片) 以张启恩、李兴源为代表的技术骨干,通过反复实践,创新了适合高寒地区的“全光育苗技术”,培育出了“大胡子”、“矮胖子”优质壮苗,解决了大规模造林的苗木供应问题。同时改进了苏制造林机械和克罗索夫植苗锹,创新了“三锹半植苗法”,提高了造林质量与速度。年4月20日,林场挑选了名精兵强将,调集了最精良的装备,开展了提振士气的“马蹄坑大会战”。王尚海带头,会战期间谁都不准回场部,大家都吃住在山上。于是,在翘尾巴河北岸,一溜儿帐篷拉起来了,一群不服输的塞罕坝人向荒原开战了。这一战就是30多天,由于连着多天不洗脸,去时的年轻小伙,回来时都变成了胡子拉碴的“小老头”。自由,终究是我们的渴望,是年轻—代的追求。自由并不是放纵,不是放荡,而是能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让思维尽情的流转,让天赋无畏的释放,让心自由自在的跟着自己的意愿而飞。在第一代林场职工陈彦娴的眼中,王尚海并不像一个“当官的”。“他没有官架子,穿得总是很破旧,常年就在普通工人堆里,一眼看去都分不出来。”正是因为这平易近人的泥土气,和身边群众共同艰苦奋斗,才留下这望不到天际的塞罕坝林场,才留下让无数人传颂的塞罕坝精神。“文革”中,王尚海的脖子上挂着5公斤重的拖拉机链条被批斗。妻子心疼,劝他辞职回老家。他说:“林场还没有建成,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坝上!”他的老战友王振兴曾问他,真打算坚持干下去吗?他说:“我连坟地都看好了,在马蹄坑,那是我参加机械造林第一块成功的林地。”年底,在亲人的悲恸中,病重的王医院的病床上用手艰难地指向北方,艰难地说出三个字:“塞……罕……坝……”这是他在弥留之际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句话。许多塞罕坝人和他一样,都把这片树林视作塞罕坝精神的象征。随着我们走进王尚海,越发对他崇拜。他是塞罕坝的“一棵松”。我们作为第一代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也要做“一棵树”,立足当下,一步一个脚印,干一行爱一行,扎根基层肥沃的土壤,用真心真情服务群众,将塞罕坝精神发扬光大,创造属于自己的无悔青春,以优异成绩向建党周年献礼。THEEND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suoe.com/llwh/9412.html
- 上一篇文章: 官方透露今年广东高考26日11点正式放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