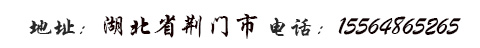圣地亚哥之路的故事最全圣地亚哥朝圣之
|
Caminode Santiago ■在耶路撒冷遇害的耶稣门徒雅各的墓为何会在西班牙被人发现? ■中世纪的朝圣者住的是“医院”? ■完成了朝圣才能挂扇贝壳,原来现在的人都挂错了? ■圣雅各的遗骨被弄丢了三百年,又是怎么被再次找到的? ■你知道这一路上的黄色箭头是怎么来的吗? ↑点击图片进入伊神 圣地亚哥(Santiago),是西班牙语里对耶稣的门徒大雅各(天主教称雅各伯)的称呼。据《圣经》记载,在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之后,他的门徒们作为使徒(天主教称宗徒),前往世界各地传教。《圣经》中并没有提及雅各究竟去了哪里,不过,许多人相信他曾到过伊比利亚,而萨拉戈萨的石柱圣母大教堂(Catedral-basílicadeNuestraSe?oradelPilardeZaragoza)中的石柱似乎可以为此事作证。根据传说,公元40年的1月2日,当雅各在这座城市停留的时候,当时还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圣母玛利亚曾亲自出现在他面前,交给他一段有斑纹的大理石柱子,并嘱咐他在此处为她建造一座圣殿。这根石柱至今仍在那里(见下图)。 石柱的背面有一小块露在外面,上方的牌子上写着“在此处敬仰和亲吻童贞圣母放置的石柱”。下方坚硬的石阶已经被虔诚的信徒们的膝盖跪出了一个大凹坑,石柱露出的部分也已经被亲吻得凹陷进去。 据传圣雅各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传教遭遇了很大挫折,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又或者是他希望在圣母永眠之前再见她一面,不久他便返回了耶路撒冷。之后据圣经记载,希律王(传统上认为是希律亚基帕一世)处决了雅各(《使徒行传》12:1-2)。关于处决所使用的工具,新教和合版《圣经》翻译成“用刀杀了”;天主教思高版《圣经》则翻译为“用剑杀了”,西方多种语言翻译及宗教图像也同样支持雅各是被用剑处决(如下图),有时认为处决方式即斩首。雅各也因此成为第一位殉教的使徒。 由丢勒(AlbrechtDürer)绘制的圣雅各殉教场景,是一组祭屏画中的一块面板。 由苏巴朗(FranciscodeZurbarán)绘制的圣雅各殉教场景(图片来源:MuseoNacionaldelPrado) 圣雅各的遗体在雅法(Jaffa)被装船(图片来源:MuseoNacionaldelPrado) 之后,根据传说,雅各的两个门徒,阿塔纳西奥(Atanasio)和特奥多罗(Teodoro)——他们也许是曾经跟随雅各一同来到伊比利亚半岛传教的人——将这位使徒的遗体装上一艘船,小船一路飘摇,穿过地中海,绕过直布罗陀海峡,又向北一路漂到加利西亚(Galicia,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北角),这才停了下来。加利西亚民间传说中的“狼女王”(lareinaLupa,也称lareinaRoba)也在这个故事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据说这位女王当时正统治着这一带,由于生性凶残,人们将她称作“狼女王”。当雅各的两位门徒请求埋葬雅各的遗体时,她毫不客气地捉弄了他们一把,向他们提供了两头桀骜不驯的公牛。然而,这当两头公牛被套上载有圣雅各遗体的拖车的时候,居然变得异常温顺起来。据说,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狼女王”大受感动,立即答应提供一处地方安葬雅各。在一些版本的传说中,她甚至为此受了洗,成为了一名基督教信徒。 收藏于普拉多博物馆的这副创作于15世纪的画作再现了这一传说中的场景:在画面远处,装载着圣雅各遗体的小船正独自飘向岸边(根据另一个版本的传说,圣雅各的无头遗体躺在一艘石头做成的船里,自己驶向了加利西亚),而在前景中,两头牛正拉着圣雅各的遗体前进,雅各的两位门徒——他们穿着15世纪时朝圣者的装束——紧跟其后。在一旁的房子里,戴着王冠、手持一面镜子的“狼女王”和她的两位随从从窗口探出头来,吃惊地看着这一切。这幅画与上一幅均出自西班牙画家马丁·贝纳特(MartínBernat)之手,可能来自同一组原本位于萨拉戈萨的圣地亚哥教堂(IglesiadeSantiagoenZaragoza)的祭坛饰屏,但其余部分已失散。(图片来源:MuseoNacionaldelPrado) 就这样,圣雅各被葬在了西班牙加利西亚的某处地方,这一睡就是七百多年。 02圣雅各成为对抗摩尔人的精神领袖 当时背景 ■罗马皇帝们最终接受了基督教,并且从迫害者的角色转变为基督教的推动者。就连那些他们眼中的“蛮族”也开始纷纷改信了基督教。因此,当最后一个西罗马皇帝于公元年被罢黜后,这些土地的新主人仍然是基督教的信仰者。不过,公元7世纪时,一个新的宗教——伊斯兰教诞生了,其传播之迅速远远超出基督教,并很快就威胁到由基督教徒统治的土地。 ■当一大群摩尔人[注]从北非入侵伊比利亚半岛时,当时半岛上的统治者是已经陷入宫廷内斗的西哥特人(Visigodos)。趁着这个机会,摩尔人短短数年时间就占领了半岛上超过四分之三的土地,只剩下北部沿海地区仍由基督徒控制。后来北方这一带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基督教小王国和伯国。 [注]:“摩尔人”(Moros)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大致等同于伊斯兰教的信仰者,即穆斯林。不过在中世纪时主要用来指出现在伊比利亚半岛、非洲北部和西部,以及地中海岛屿上的穆斯林,包括含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在内的多个民族。 公元年时的伊比利亚半岛,其中绿色部分均属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倭马亚(也译作伍麦叶)王朝,仅北部沿海地区仍由基督徒控制。 公元9世纪时的某一年(有人说年,有人说年,还有人索性折中一下说年左右,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会再次提到),有一位名叫佩拉约(Pelayo,Paio或Pelagio)的隐士夜观天象,发现有一道异光,似乎在指向森林中的某处地方。于是,他当即向住在伊里亚·弗拉维亚(IriaFlavia,即今天的Padrón帕德隆)的主教特奥多米罗(Teodomiro)汇报了这件事。主教跟随着这道异光进了森林,发现那里有三座古坟,其中一座明显看上去要比另两座醒目。主教接连斋戒默祷了三天,最终得到启示:他眼前所见的,正是耶稣门徒雅各的墓。人们就是这样解释圣雅各之墓的发现的。 圣地亚哥大教堂正立面从上数下来第二层便是关于雅各之墓的故事。位于左右两侧的是雅各的门徒阿塔纳西奥和特奥多罗,他们都穿着朝圣者的装束。位于中央的是雅各的棺椁,由天使环绕着,其上方是指引人们找到它的那颗星星。(图片来源:WikimediaCommons/PMRMaeyaert) 接着,主教又向阿斯图里亚斯王国(ReinodeAsturias)的国王阿方索二世(AlfonsoII)通报了这个奇迹,国王立即下令在发现雅各之墓的地方建造一座小教堂。据记载,那是在年。阿方索二世也成为了第一位前去朝圣的国王(如果他本人确实去过的话)。70年之后,也就是年,国王阿方索三世(AlfonsoIII)觉得之前的教堂太小了,于是又拆了重建了一座更大一些的。这两座教堂所在的地方,后来就发展成了今天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deCompostela),通常简称为“圣地亚哥”或“孔波斯特拉”。关于“孔波斯特拉”的意思,浪漫派认为这个词有点像拉丁语中的“星之原野”(CampusStellae),因为人们就是遵循星光的指引而找到它的;而现实派则认为这个词来自拉丁语中的“墓地”(Compositum)——它本来就是。 之后,一场被认为是凭空臆想出来的战役——历史学家甚至不屑于去讨论它的真实性——克拉维霍之战(BatalladeClavijo),使得圣雅各成为了(至少是一度成为了)西班牙人眼中最为重要的圣人。这场虚构的战役被设定在阿斯图里亚斯国王拉米罗一世(RamiroI)统治时期的年5月23日,作为最终取得胜利的一方,拉米罗的战果只是从此以后不用每年向摩尔人进贡个处女(tributodelascienvírgenes)。这听上去很荒唐,但战争本身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圣雅各本人出场了。据说,拉米罗和他的军队被围困在克拉维霍城堡,夜里,拉米罗做了一个梦,梦中圣雅各向他许诺会帮助他取得胜利。而第二天,当拉米罗带着他的军队勇敢地冲出城堡时,这位圣人果然出现了,他骑着一匹白色的战马,帮助这位国王将摩尔人杀了个落花流水。 《使徒雅各在克拉维霍之战前在拉米罗的梦中显现》,由19世纪菲律宾画家FélixResurrecciónHidalgoyPadilla绘制。(图片来源:MuseoNacionaldelPrado) 《在克拉维霍战场上的圣雅各》,由19世纪西班牙画家JoséCasadodelAlisal绘制。 于是,圣雅各被赋予了一个全新的身份:他不再仅仅是一名使徒,而且还是西班牙人眼中的“摩尔人杀手”(SantiagoMatamoros)。人们在西班牙很容易看到以这种形象出现的圣雅各:他威风凛凛地骑在一匹白马上,挥舞着手中的长剑;裹着头巾的摩尔人在他的马蹄下东倒西歪,有些还掉了脑袋。 在正对着圣地亚哥大教堂的拉霍伊宫(PazodeRaxoi)的最顶端,就是一尊巨大的“摩尔人杀手圣雅各”的雕像。他骑在马上挥舞着剑,马身下方是无力抵抗的摩尔人。(图片来源:WikimediaCommons/LuisMiguelBugalloSánchez) 在这里还有必要再补充几句:第一,“克拉维霍之战”的传说可能是在12或13世纪时才被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在拉米罗统治时的9世纪。它最早出现于一本13世纪的编年史中的一个被认为是虚构的章节,并且似乎与圣地亚哥骑士团(OrdendeSantiago)的诞生存在一定联系;第二,圣雅各并不是唯一一个“骑着白马现身战场,帮助基督徒剿灭摩尔人”的圣人。除了阿斯图里亚斯,另两个基督教古国——卡斯蒂利亚(Castilla)和阿拉贡(Aragón)也不甘示弱地宣称得到了骑白马的圣人骑士的帮助。圣米扬(SanMillán),一位西班牙本土出生的隐修者,在年的希曼卡斯之战(BatalladeSimancas)中帮助了卡斯蒂利亚;圣乔治(SanJorge),那位以“屠龙救公主”的传说闻名的骑士,则在年的阿尔科拉斯之战(BatalladeAlcoraz)中帮助了阿拉贡。 在年的希曼卡斯之战(BatalladeSimancas)中骑着白马举着十字旗,帮助卡斯蒂利亚战胜了摩尔人的圣米扬(SanMillán)。 “摩尔人杀手圣雅各”,这个在战争中被创造出来的英雄形象具有现实的鼓舞意义。起初,位于半岛北部的基督教领地只是一些各自为政的小国家,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国王对于国家统一似乎缺乏关心,当一个国王有三个儿子的时候,会习惯于将国土一分三份,每个儿子都得到一份,女儿们也能得到一些。之后,兄弟们又会互相觊觎彼此的土地,想方设法登上对方的王位。就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方诸国合了又分,分了又合。而现在(如同前面说过的,最早也是12世纪起),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联合起来了,这个目标就是将整个半岛从伊斯兰教的统治者手中夺回来。圣雅各成为了西班牙的守护圣人,当基督徒的军队向摩尔人发起进攻时,士兵们高喊的口号不是“冲啊!”而是“圣地亚哥!”(?Santiago!) 意大利画家提埃波罗(GiovanniBattistaTiepolo)绘制的圣雅各 然而,有圣人助阵,也未必每次都能得胜。一位令人闻风丧胆的摩尔将领,以摄政名义独揽大权的阿尔曼苏尔(Almanzor,-2),率领着他的军队挨个儿教训了北方的基督教诸国,摧毁了一座又一座重要城市。年,他的军队开进了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发现迎接他们的竟是一座空城。原来,早知抵抗也是徒劳的圣地亚哥主教佩德罗·德·门松索(PedrodeMezonzo)紧急疏散了全城居民。8天之内,包括圣地亚哥教堂在内的一切都被大火烧成了废墟。这还不够,为了羞辱基督徒,阿尔曼苏尔又召来一群俘虏,强迫他们扛着教堂的大钟,徒步运送至千里之外的科尔多瓦清真寺(MezquitadeCórdoba)。今天我们看见的大教堂(Catedral),已经是在这片土地上建起的第三座了。它始建于年,完成于年,为罗曼式风格。新的正立面则是18世纪时的巴洛克作品。 13世纪时的朝圣们看到的大教堂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图片来源:artehistoria. 10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王国的边界又向南扩张了一些,昔日的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将首都迁至莱昂(León),改称莱昂王国(ReinodeLeón)。卡斯蒂利亚伯国(CondadodeCastilla)的首都设在了布尔戈斯(Burgos),而潘普洛纳王国(ReinodePamplona,纳瓦拉王国的前身)则因年潘普洛纳城被穆斯林军队摧毁,而将宫廷迁至新近征服的纳赫拉(Nájera)。于是,以这三座都城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四点一线,一条新的朝圣路诞生了。这条路也正是今天最多人选择的道路。与位于北部海边和山区的朝圣古路相比,这条位于高原的道路要平坦不少,尽管仍有几个山口需要翻越,但能更快更容易地抵达。同时,广阔的地貌也更有利于发展规模较大的城市。对于基督徒的“收复失地运动”(laReconquista)来说,抢夺土地还不算太难,守住战果才难。如果新“收复”的土地无人居住,那么就很容易再被摩尔人抢回去。通过“朝圣之路”吸引外国人(多数是法兰克人)前来,再通过赋予某些城镇特权吸引他们留下来定居、做生意,一座座城镇就这样在道路沿线发展并富裕起来。 位于莱昂与圣地亚哥之间的小城蓬费拉达(Ponferrada)就是一个完全依托圣地亚哥之路而建立起来的城镇。尽管人类在此生活的痕迹可以追溯到远古,但在穆斯林入侵后这里显然已是一片荒芜。11世纪时阿斯托加(Astorga)主教下令在锡尔(Sil)河上架设桥梁帮助朝圣者抵达圣地亚哥,之后河的两岸逐渐形成村落。12世纪时圣殿骑士团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城堡(CastillodelosTemplarios,即上图),之后莱昂国王又赋予该地诸多特权以吸引人们定居,于是,一座拥有商业区、农田、手工作坊和城墙的像模像样的城镇就这么诞生了。(图片来源:WikimediaCommons/JoséLuisFilpoCabana) 11世纪的时候,朝圣者已经能无所顾虑地从纳赫拉一路走到圣地亚哥。一位名叫多明我·加西亚(DomingoGarcía)的修士因毕生致力于修建从罗格洛尼奥(Logro?o)通往布尔戈斯的宽敞大道而在死后被封圣。他与同伴一起,一路砍伐森林、开垦土地、架设桥梁,后来人们将他称为DomingodelaCalzada,也就是“修大路的多明我”,“calzada”就是有平整铺面的大公路的意思。 在以这位修路圣人的名字命名的小城SantoDomingodelaCalzada的大教堂内设有一个鸡笼,常年饲养着一对白色的活鸡,成为了这条充满了传说的路上最有趣的一景。据说很久以前一位年轻的朝圣者因拒绝了姑娘的求爱而被诬陷偷窃,他被判处绞刑但却奇迹般地没有死。判他刑的长官不相信这事,嘲笑说这就像是他盘中的鸡。结果,两只已经被烤熟的鸡当场复活。(图片来源:catedralsantodomingo. 在法国那边,有四条主要的朝圣道路,它们分别连接着一些热门的朝圣地,这些地方都珍藏有重要的圣人遗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走哪一条。对于一名中世纪的朝圣者来说,朝圣之路并不是通往唯一终点的漫漫长路,他们甚至不一定需要抵达圣地亚哥,沿途的重要圣地同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为了能看到某件著名圣物,人们往往不惜绕路。12世纪时甚至诞生了一本著名的朝圣指南,书中贴心地罗列了一路上朝圣者们不容错过的圣人遗物和它们的所在地、路上可能会遇到的危险、途经的河流的情况和水质、村庄和城镇的名字以及各地的风土人情。最后还用大量篇幅详细介绍了圣地亚哥城以及大教堂的细节。 这本朝圣指南与其它4卷独立的、不同时间完成的书一起组成了一部合集《圣雅各之书》(LiberSanctiIacobi),并被广泛地抄写和流传,现今仍存12本左右。其中最古老的一个抄本(约完成于年前后)现收藏于圣地亚哥大教堂。 这本被以教宗嘉礼二世(CallixtusII)之名命名的《圣雅各之书》现存最古抄本《CodexCalixtinus》后来被证实书中托此位教宗之名所写的书信作者另有其人,且教宗本人在年就已经去世了。(图片来源:WikimediaCommons/Manuel) 顺便说一句,有关圣雅各曾在查理曼(Charlemagne)的梦中显现,请求查理曼“循着银河的指引”找到他的墓并将其“从摩尔人手中解救出来”的传说就出自这部合集的第四卷(即上图中打开的页面),这卷书讲述了查理曼出征西班牙的一些故事和传说,还包括骑士罗兰的故事。作者是一位借用了兰斯大主教托平(Turpin)身份的佚名人士,被称作伪托平(Pseudo-Turpin)。查理曼死于年,因此,将发现圣雅各之墓的年份提早到或年很可能是为了配合这个传说(并且这样的话,雅各墓的首位发现者就变成了查理曼)。另三卷书则分别是关于宗教仪式、和圣雅各有关的神迹,以及这位使徒的遗体是如何运至加利西亚的。 人们抱着各自不同的目的踏上了朝圣之路,有的为了祈福,有的为了赎罪,有的为了治病,有的希望灵魂获得永生。除此之外,朝圣还给了当时的人们尤其是普通百姓一个难得的旅行机会,就连妇女都有机会出门远行。后来,朝圣活动从三三两两的自发行为发展成了有官方组织的集体旅行。大教堂18世纪的正立面上的圣雅各雕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已经抵达圣地亚哥的中世纪朝圣者形象:他戴着大檐帽、披着斗篷、手里拄着挂着葫芦的手杖,还背着一个朝香袋(或者说是朝圣者的旅行包)。他的左手还握着一本书,但这个不属于朝圣者的标配,而是他使徒身份的象征。 在过去,雅各的形像和其余11位使徒一样,都穿着长及地面的多褶长袍,一手拿书——使徒的身份象征,另一手拿着各自受难的刑具——对于他来说就是一把剑,因为他死在剑下。奥伦塞(Orense)的圣马丁大教堂(CatedraldeSanMartín)中的一座13世纪的圣雅各像(见下图)就是其中一例。自从有了朝圣者装束后,雅各也成为了十二使徒中最容易被辨认出的人。 (图片来源:WikimediaCommons/Pylaryx) 扇贝壳在12世纪的《圣雅各之书》中已经得到记载作为这位使徒的象征。起初,扇贝壳还被用作完成朝圣的唯一证明,只有当朝圣者抵达圣地亚哥之后,才能带回一枚从加利西亚的海边捕捞上来的珍贵扇贝壳,而此物在除圣地亚哥以外的任何地方均禁止售卖。正因如此,在中世纪教堂装饰中出现的佩戴贝壳的朝圣者形象代表的是已经去过圣地亚哥的人,而不是还没到达圣地亚哥的人。当时的人们很熟悉这一点。而现在,人们往往还没上路就会先往自己的背包上别上一枚(也不知产自哪里的)扇贝壳,因此完成朝圣不得不另由一纸朝圣证书来证明了。 圣雅各的另一个符号是“圣地亚哥十字”或称“圣雅各十字”(CruzdeSantiago)。同样是自12世纪起,路上的朝圣者们有了圣地亚哥骑士团的骑士们的保护和帮助。骑士团最初的纹章是一个在中心和四个端点都装饰着扇贝的十字架,后来便改成了这个人们在这条路上最常看见的“圣地亚哥十字”。这个十字架形似一柄利剑,象征了雅各的双重身份:作为骑士,那个人们口中的“摩尔人杀手”,剑是骑士的武器和标志;作为使徒,剑是他受难的刑具。 圣地亚哥十字 在获得圣地亚哥骑士团骑士荣誉后,委拉斯凯兹(DiegoVelázquez)在自己的名画《宫娥》(LasMeninas)中的自画像上补画上了这个大大的“圣地亚哥十字”,当时这幅作品早已完成。与贝壳一样,当时这个十字图案并不像现在这样每个人都可以随便得到。 随着朝圣人数的爆炸性增长,沿途的修道院再也接济不了更多的穷人和病患了。于是,医院应运而生,为路上往来的人们提供了精神、肉体和卫生三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西班牙语中的“hospital”(医院)和“hostal”(旅舍)这两个单词拥有完全一致的词源,即拉丁语中的“hospitālis”,这个词有类似“收容所”的含义。医院医院和旅舍这两种功能合二为一的建筑,常常作为修道院的附属建筑,由修士和修女们负责打理。朝圣者和穷人、病人们既能在这里歇脚,又能得到治疗,还能得到精神上的抚慰。其开销主要来自宗教机构、贵族和富人们,尤其是国王们的捐赠。小型的医院习惯在房间里设置12张床位,用以纪念12使徒。一部分医院被保留至今,依旧为朝圣者提供住宿,但却不再提供医疗服务。还有一些则被西班牙国营酒店集团(ParadoresdeTurismodeEspa?a)收购,摇身一变成为了高档酒店,高昂的房价几乎将真正的朝圣者群体拒之门外,反而成为了休闲度假游客的奢华之选。 医院,来自15世纪的手抄本绘画(图片来源:artehistoria.位于圣地亚哥大教堂左侧的“医院”(HospitaldelosReyesCatólicos),现在已经将名称中的“hospital”替换成了“hostal”,从而变成了“天主教双王旅馆”,尽管这两个词本来是同一个意思。这座建筑由“天主教双王”――阿拉贡的费尔南多和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尔下令建造,用于向贫穷的朝圣者和弱势群体提供庇护、医疗和短期免费住宿,然而现在它是一座当年的那些穷人们绝对住不起的豪华五星级酒店。(图片来源:WikimediaCommons/AngelTorres) 13世纪时,朝圣活动达到全盛。在之后的14-15世纪,由于西方教会大分裂、百年战争、黑死病、饥荒和经济危机等因素,朝圣人数有所下降。不过,14世纪末至15世纪时,一条“海上朝圣路”繁荣了起来。装载着大批朝圣者的船只挤满了拉科鲁尼亚(ACoru?a)的港口,从这里人们只需步行不到80公里就可以抵达圣地亚哥。 世纪:宗教改革和朝圣之路的衰落 当时背景 ■经历了漫长的“收复失地运动”、驱逐没有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年)和穆斯林(年),西班牙终于实现了宗教上的统一。所有留下的人,不管是诚心的,还是被强迫的,现在都已经是天主教徒了。然而很快,宗教改革再度撕裂了天主教,西班牙开始极力镇压新教并阻止其在境内传播。 ■宗教改革人士批判天主教教堂里里外外布满各种或是石雕、或是木雕的像,是犯了“不得雕刻、崇拜偶像”的大罪;对圣母及圣徒的崇拜(天主教徒则辩解称这只是崇敬而非崇拜)又违背了一神论。宗教改革运动期间,大量圣像被毁。在反宗教改革人士强硬镇压的同时,新教徒采取暴力行动对抗,烧毁教堂和修道院,抢劫教会财产。许多教堂中收藏的圣人遗物和遗骨被清除出教堂,并遭毁坏丢弃。 ■西班牙与法国的战争,以及出于防止路德教传入境内的考虑,使得西班牙封锁了边界,这意味着朝圣者不能再自由地从法国进入西班牙。 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军人物:马丁·路德(MartinLuther)、加尔文(JeanCalvin)和慈运理(HuldrychZwingli) 中世纪的人们对于圣物的狂热让商人们嗅到了商机。圣物是如此受欢迎,又是如此容易卖出高价,但其真假往往不得而知。有关基督和圣母的遗物众多,包括基督的血和眼泪,圣母的乳汁、腰带和衣物,以及基督幼年时期留下的物品:乳牙、脐带和包皮(有两处教堂声称拥有基督的包皮),而数量最多的则是基督受难时被钉的“真十字架”的碎片。16世纪时的改革派教徒常常不无嘲讽地提出质疑,劝诫人们不要长途跋涉去崇拜那些“可疑的”物品,并且“错误地”将其认作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伊拉斯谟(DesideriusErasmus)尽管终生都是天主教徒,但也毫不避讳地指出,“欧洲所有的真十字架遗物可以装满整整一船”。 路德指出,救恩是上帝的恩典,是祂白白给予人类的礼物。他认为,这救赎并不是透过善功,而是单单藉信靠耶稣基督作为救赎者而获得的。由此,他多次严厉地谴责朝圣活动,认为天主教会倡导的这些做法属于“因行称义”,是试图“贿赂”上帝的错误且有害的行为。加尔文和慈运理也同样反对各种形式的朝圣和宗教游行。 一幅关于年发生在苏黎世的焚毁圣像的插图。事实上,多数摧毁教堂中圣像的行动都比画中描绘的要野蛮得多。 路德、加尔文等宗教改革人士在脱离罗马天主教会的同时,也从天主教信徒中带走了大批追随者,从而有了基督教新教各宗派。欧洲部分地区的天主教教堂被改作新教教堂,圣像和圣人遗物均被清理了出去。英格兰的情况又有所不同,英王亨利八世(HenryVIIIofEngland)原本是路德的反对者,但当他因王后没有生下男孩而想要休妻遭教宗拒绝时,便一气之下脱离罗马教廷,成立英格兰国教会(圣公会),将自己立为教会首领。而荷兰则在经历了一番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之后彻底地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取得独立——无论是在自由方面还是宗教信仰方面。在宗教改革取得胜利的国家和地区,前往西班牙朝圣的人数一度直降为零。 年8月8日的海战中,英国海军摧毁西班牙“无敌舰队”。 年8月8日,向英格兰宣战的西班牙“无敌舰队”(ArmadaInvencible)意外地栽在了由“英国海盗”率领的小船队手中。次年5月,由曾参与击溃“无敌舰队”的海盗头子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Drake)率领的船队又袭击了离圣地亚哥不远的港口城市拉科鲁尼亚。出于恐慌,大主教胡安·德·圣克莱门特(JuandeSanclemente)秘密转移了大教堂中的圣雅各遗骨,没有人知道其藏匿地点。 这件事当然还有后续,不过那已是将近三百年之后了。年,红衣主教米盖尔·帕亚(MiguelPayáyRico)决心要找到已经丢失了几个世纪的的雅各遗骨,于是组织了一系列对教堂地下的发掘行动。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人们在教堂后部区域的地下挖出一个装有人骨的容器。年,教宗利奥十三世(LeoXIII)颁发教宗诏书《DeusOmnipotens》,郑重向整个天主教界宣布这次被发现的就是使徒圣雅各本人的遗骨。这次事件也被称作“第二次发现”(ElSegundoDescubrimiento)。 关于这件事,很多书和网站都没有作详细说明,几句话就给一笔带过了。不过这样可能有人就要问了,那怎么就知道这次挖出来的就是圣雅各的遗骨呢?而且,在对大教堂地下的考古发掘工作中,挖出来的可不止一个人的骨头,还挖出了一个古罗马时代的大坟场。从公元1世纪起至5世纪,这里都被用作墓地。因此在这篇文章里我再多补充几句,尽管名声最大,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并不是唯一一处声称拥有圣雅各遗骨的地方。据相关记载,为了证明这次“发现”的可靠性,使用的比对物是收藏于意大利皮斯托亚(Pistoia)大教堂内的圣雅各遗骨碎片,但当时的检测手段肯定没有现在先进。而朝圣路上的著名教堂之一——图卢兹(Toulouse)的圣瑟尔南(Saint-Sernin)教堂拥有的众多圣人遗物清单中同样也包括了这位使徒的遗骨。考虑到遗体的可分割性,这种情形并非没有可能。此外,英国的里丁修道院(ReadingAbbey)也声称在他们的超过件的圣物收藏中包括圣雅各的一条胳膊,18世纪时人们清理这座修道院的废墟,还正好找到了一条风干的胳膊。 -20世纪:朝圣之路的浴火重生 圣雅各的银棺细节。这个看起来像是12世纪风格的银棺实际上是19世纪晚期制作完成的。 尽管圣雅各的遗骨缺席了将近三百年,但还并没有直接终结朝圣的历史。与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发生的众多变故相比,这一事件的影响甚至都算不上大。17世纪,当阿维拉的德肋撒(TeresadeJesús,又称耶稣的德兰或大德兰)被封圣后,她的追随者们曾试图推选这位本土出生的圣女取代圣雅各,作为西班牙国家的主保。因为那时,西班牙面临的威胁来自新教徒,而不是他们已经解决了的摩尔人(不过最终,使徒保住了他的地位)。同样还是在17世纪,年-年间,西班牙身陷“30年战争”,这场源于宗教冲突的战争几乎殃及整个欧洲。另外,17-18世纪时,神圣罗马帝国(今天的德国及奥地利)的一些朝圣地点成为了新热门。由极尽华丽繁复的巴洛克和洛可可式装饰装点的朝圣教堂令人眼花缭乱,蜂拥而至的朝圣者人数甚至是今天去圣地亚哥朝圣的人数的两倍。除新教徒外,启蒙运动者也对这种朝圣狂热予以强烈谴责,将其斥为愚昧的迷信活动。最终,“回归理性”的人们开始放弃朝圣。 再回到18世纪的西班牙。-年,由于哈布斯堡王朝绝嗣爆发了王位继承战争,最终,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利普登上了西班牙王位。之后,西班牙虽仍被卷入一些战争,但已经意识到需要重振经济。圣地亚哥大教堂也正是在这段时期里建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巴洛克式正立面。 -1年间,圣地亚哥大教堂进行了一次重大“装修”:重建了正立面。新的正立面为巴洛克式,出自费尔南多·卡萨斯·伊·诺沃阿(FernandoCasasyNovoa)之手,完全盖住了教堂原本的罗曼式外观。但这也正是建造新立面的原因之一,即保护珍贵的“荣耀门廊”免受风雨侵袭。正立面前方的广场原本是建造大教堂时的石匠工坊所在的区域,因而得名“工坊广场”(加利西亚语:PrazadoObradoiro),这个立面也因为朝向此广场而被称作“工坊立面”(FachadadelObradoiro)。 由英国画家大卫·罗伯茨(DavidRoberts)绘制的19世纪30年代的圣地亚哥城景象 和平稳定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年,法国爆发了举世闻名的大革命。在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之后,西法之间又打了一仗,而紧随其后的战争还包括由拿破仑的军队入侵西班牙引发的西班牙独立战争、西班牙国内的革命战争,以及费尔南多七世去世后因继位问题而引发的三次“卡洛斯战争”(GuerrasCarlistas)。换句话说,在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晚期的将近一百年里,圣地亚哥之路所经过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西法边境省份,几乎都沦为了战场。圣地亚哥的地位也逐渐旁落,零星来访的朝圣者几乎只有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第一次卡洛斯战争中,发生在西法边境城市伊伦的战役(BatalladeIrún,) 朝圣之路上的古城埃斯特亚(Estella)也是卡洛斯战争的战场之一。以上为第一次卡洛斯战争中的枪决以及第三次卡洛斯战争中的保卫战 在下一个一百年里,西班牙又迎来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内战的爆发更是将这个国家一分为二。这期间还伴随着大量毁坏教堂和修道院的行为。与此同时,其它一些国家则遭受着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伤痛。很长时间以来,圣地亚哥之路几乎被人遗忘,沿途的道路、桥梁和设施的损毁也不足以支持人们完成一次长途朝圣。 20世纪50-60年代时,圣地亚哥之路的重建工作被小心地提上日程。但至70年代时,每年总共的朝圣人数仍只有几十个,少的时候甚至只有十几个。即使是在“圣年”(A?oSantoJacobeo:如果这一年的7月25日恰逢星期日,这一年就是“圣年”),全年的朝圣者也不过几百人。朝圣之路真正的复兴还要从上世纪80年代末算起。到年时,年朝圣人数终于接近一万,而接下来的年“圣年”,这一人数几乎翻了十倍。也正是在这个“圣年”,圣地亚哥之路的“法国之路”(ElCaminoFrancés)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一条目在年和年又扩充了法国和西班牙境内的其它几条线路。“世遗”的殊荣显著提高了圣地亚哥之路的影响力,在最近的一个“圣年”,即年,朝圣的人数超过27万,但这一纪录已经被和这两个“普通年”打破。 在教堂最末端的一个不太起眼的区域,有一扇小小的“圣门”(PuertaSanta),又称“宽恕之门”(PuertadelPerdón),平时被用石头从背面堵死,只有当“圣年”到来时,才会重新打开,这一开就是一整年。不过,若想赎清罪过,光从“圣门”中穿过是不够的,还需要完成规定的一系列步骤。上一个“圣年”为年,而下一个“圣年”则是年,再下一个为年。(图片来源:WikimediaCommons:MarisaLR/IttoOgami;caminodesantiago.gal) “黄色小箭头之父”ElíasVali?a在塞夫雷罗小镇的雕像(图片来源:blog.caminofacil.net) 今天的人们能够一路顺利地抵达圣地亚哥,还需要感谢一个人。他的真名叫作埃利亚斯·巴利尼亚(ElíasVali?aSampedro,-),生于萨里亚(Sarria),因其职业而被人称作“塞夫雷罗的神父”(OcuradoCebreiro)。这位终生致力于复兴圣地亚哥之路的学者不仅完成了一篇相关的博士论文、亲自撰写了一本朝圣者指南、参与了大量重建工作,还“创造”了著名的黄色箭头。那是上世纪80年代,圣地亚哥之路刚刚复苏时,在塞夫雷罗做神父的巴利尼亚不断听到朝圣者诉苦说他们这一路老是迷路,于是,他带上一堆桶装黄色油漆,开着自己的雪铁龙汽车一直抵达西法边界,在“法国之路”的数百处容易迷路的地点画上指向圣地亚哥的黄色箭头。选择黄色,是因为这种颜色更为显眼。关于他还有一则趣闻流传了下来:当他一个人提着黄色油漆桶在比利牛斯山区被国民警卫队拦下时,他们质问他在如此靠近法国边境的地方打算做什么?这位神父幽默地回答道:“在为一次从法国来的大入侵做准备。”于是他被带走了。不过后来他解释清楚了这一切。 巴利尼亚的这项工作开始于年,5年之后他就因病去世了,而对于整个庞大的“圣地亚哥之路”网络来说,这项做标记的工作还远未完成。弥留之际,巴利尼亚不忘嘱付他的家人,千万不要让黄色箭头失去它的作用。现在每一个踏上圣地亚哥之路的人都会一路寻找那些指引方向的黄色箭头,其中有一些是巴利尼亚本人绘制的,另一些则是由他的家人和志愿者们完成的。它们已经和贝壳一起,成为了这条朝圣之路的标志和象征。 人们熟悉的黄色箭头(图片来源:blog.caminofacil.net) 位于塞夫雷罗小镇的ElíasVali?a纪念碑,以及他在小镇教堂中的墓(图片来源:xacopedia.塞夫雷罗小镇的标志性景观“Palloza”,其起源可追溯到凯尔特人时期。但小镇自16世纪起便日渐衰败,至19世纪时已几近荒废。ElíasVali?a同时也是推动小镇重建工作的重要人物之一。(图片来源:WikimediaCommons/SanchoPanzaXXI;xacopedia.圣地亚哥之路上的伊拉切修道院(MonasteriodeIrache)对面的伊拉切酒庄(BodegasIrache)为朝圣者提供免费的葡萄酒。不过,如果想要带一些路上喝的话,则需要付费。(图片来源:WikimediaCommons/JoséAntonioGilMartínez) ?BuenCamino! 喜(Zàn)欢(Shǎng)作者 ↓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suoe.com/lldx/7886.html
- 上一篇文章: 环球疫情下南美纸业新一轮投资潮
- 下一篇文章: 世卫警告抗疟疾无进步病亡人数或因新冠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