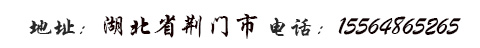于坚写诗,就像手艺失去了谋生能力丨棕皮手
|
白癜风的图片 http://m.39.net/pf/a_6344211.html撰稿︱于坚全文共字,阅读大约需要5分钟通过修补瓷器的经历,诗人于坚认为,世界诞生了一种可怕的美:全新的才是好的。在这个时代,写诗就像手艺一样,早已失去了谋生的能力。但诗人通过语言,将记忆、经验、知识焊接起了不同的时代,让文明获得了意义…… 年,曼德尔施塔姆写下了一首题为《世纪》的诗: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直视你的眼睛 用他自己的血焊接 两个世纪断裂的椎骨? 他提到了“断裂”和“焊接”这两个词。诗人干不了断裂这种事,诗人的工作是焊接。焊接相当具体:世纪的断裂,乃是意义的断裂;诗人的焊接是通过词,词不是意义,词是一种粘合剂。通过粘合、焊接,词再生。时代作为意义会过时,但词穿越时间。词是材料,材料可在任何时间中用。比如“时代”这个词,在某个时代的意思是莺歌燕舞,曼德尔施塔姆的时代却是一头野兽。而且在不同读者中,这个词的意思也不一样。在曼德尔施塔姆那里,这个词或许意味着绝望;而对于彼得堡的某位沙俄时代的贵族来说,这个词只意味着男仆藏在旧袜子里的破洞。所以,曼德尔施塔姆的这几行诗未免武断,读者被推入判断而不是感受。 曼德尔施塔姆档案 曼德尔施塔姆表达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这种焊接,后现代很时兴,将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时间在一件作品里面组合起来,生出新的审美空间,比如法国的杜尚、德国的博伊斯、美国的劳森伯、日本的白南准。再比如阿尔托。宋代黄庭坚的“点石成金”,也是一种焊接。什么石头都可以,重在成金,升华成第三个东西。 焊接,意味着世界是荒诞的,而不是正确的、非此即彼的,而是风马牛不相及、各得其所一堆杂件。 阿甘本从价值的层面来理解焊接,他说:“诗人——必须为他的当代性付出生命的代价——不得不把他的凝视牢牢地固定在他的世纪——野兽上,他必须用自己的血来焊接时代断裂的脊骨。两个世纪,两个时代,不只是已知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同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单独个体的生命长度(世纪原本就意味着一个人生命的时期)和集体的历史时期——在这里,我们称之为二十世纪。”个人的价值和公共的价值。 诗人的血是什么?就是语言。诗的焊接是辽阔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记忆、经验、知识,都是待用的材料。焊接就像一位巫师,在祭祀中调动一切可以引起神灵注意的因素,营造出一个场。兴观群怨、迩远多识,就是场,以实现有无相生、语言的不可说之说、语言之有对无的勾引。我以前写的长诗《0档案》,也是一种焊接,将各种历史的、当下的、俗语、陈词滥调、口语、标语、私语、恋人絮语、书面语——风马牛不相及的词焊接在一个空间中,令它们彼此反对,戏仿,解构,寻找,肯定。 现代是一个废墟。古代世界的完整性已经土崩瓦解,成为碎片。毕加索、杜尚的出现,绝非偶然。而且,断裂一场接着一场。焊接刚刚完成,又断裂了,后现代就是焊接。 《于坚集·0档案·长诗七部与便条集》罗兰﹒巴特将这种碎片的再生叫做“改编”,“无风格作家的典型,是纪德,他用手工方式将某种从古典主义的精神中开掘的现代情理,完全像圣-萨爱恩改编巴赫的作品,或布朗克改编舒伯特作品那样。”(罗兰﹒巴特《什么是写作》)改编,就是解构的重组、意义的重读。这种重组,将原作视为废墟。在11世纪,黄庭坚就意识到这种经典作品的废墟化:“点石成金”。在黄庭坚看来,古典作品的完整性已经成为某种石头般的废墟,在重组中借尸还魂。重组必须焊接,重新意味着从成品回到手工。完成的作品曾经上手,完成意味着手工的丧失。 焊疤是上手的结果。废墟在这种连接中获得一个疤痕,现代写作无不密布这种疤痕,乔伊斯、普鲁斯特、基弗、黄宾虹,毕加索,波德莱尔…… 这种疤痕不是推到重来、复〇,而是接着说。钢接着铁说。锡接着陶说。野兽接着时代说。 焊接,历史不能总是猴子掰苞谷式地总是从〇开始,将世纪的断裂焊接起来,比断裂更高级,让意义再次回到材料。处理材料,而不是处理意义。不是“观念的冒险”,而是对材料的一次次再阐释。雕塑家罗丹说,用旧词就够了。 本文作者于坚。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写作至今,著作四十多种。系诗《尚义街六号》《〇档案》《飞行》《巨蹼》、散文集《挪动》《巴黎记》、摄影集《大象.岩石.档案》、纪录片《碧色车站》等之作者。拆迁轻而易举,焊接很难,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手工,而且必须有灵感。 我有一次在纽约看见一件作品,放在一个橱窗里,作者用一堆不锈钢调羹做了个印第安酋长的头像,建构材料还包括羽毛、玉米等。那些作为印第安人王者标志的羽冠,全部用不锈钢勺子做成,一个有力的转喻,勺子的造型与羽毛近似,而且它是“不锈”的,也即不朽的。 世纪会成为废墟,烟消云散,意义也一样。但,语言却能够穿越了无数世纪。“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代悲白头翁》)语言正是这种花。语言都是一个语言,从甲骨文到现在,都是汉语,但每个作者、时代说法不同。重在说法,不在含义,含义会变化、易位、死去,而语言不死。语言,这是人之为人的合法性所在。 人是语言动物。语言就是一切。焊接就是说法,废除原义,生发新义,但材料不变。铜和铁可以焊接在一起,要点是你得用它们都能接受的温度、焊材、手艺。这是一种莫若以明(庄子)的焊接。 焊接这个活计我相当熟悉,16岁时我在一家工厂的铆焊车间做工,活计之一就是焊接。电焊,氧焊,我都干过。不同的材料,或者相同但断裂了的材料,通过某个熔点,焊接会产生第三种东西,焊接不能改变两种材料的性质,但将它们连接在一起,模仿着它们本具的密度。就像是一种转喻,材料和材料之间的相似性、临近性。比如将汽车和甲壳虫这两个词连接在一起,不仅外表有某种相似,密度也有某种相似。一辆甲壳虫般的汽车,汽车本具的某种速度、质地被敞开了。它就是甲壳虫那种速度,那种不堪一击的坚硬,那种上帝视界中的慢吞吞。公路边经常斜歪着许多甲壳虫般的汽车,被忽然失去了理性的方向盘踩瘪了(它变成了一只疯狂的铁蹄)。但它确实不是甲壳虫。方糖般的小汽车,令纽约就像是一个小男孩。临近性在于速度,溶化般的缓慢,也是上帝的角度。有一次,我在摩天大楼的顶上看着这些方糖在街角融化,不见了。那些方糖花花绿绿,玩具般的可爱。任何事物在一定距离内都会变成它不是的东西,感受不同了,蚂蚁般的汽车。 纽约几年前,我在昆明古玩店买到一个云南建水紫陶花瓶,是民国早期名家戴得兴的作品,器型相当美,像是一个中年贵妇(瓶子的腰身与妇人的腰身有某种临近性),梅花画得很老道,瓶身还有几行字:“盖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谓不朽,抑又闻之,端揆者,百寮之师。”这是颜真卿《争座位贴》里的一段。颜真卿的文章写得很好,《麻姑仙坛记》、《竹山堂连句》都是相当好的散文。但是,他的意思被他的字遮蔽了。颜真卿,就是写个粪字也是美的,中国书法具有一切艺术所达不到的超越性,完全不着相,或许只有巴赫能够与之相提并论。戴得兴大概练过颜真卿,这几个字也是学颜体。这些字和那个瓶面上的梅花做工相当复杂,先在陶泥上画出小稿,然后照着线条挖刻出缝,再在缝里面填上白泥。烧制出来,陶瓶本色和画就是两个颜色,一黑一白。知白守黑,对材料的处理方式意味深长。而画梅花的手法是另一种知白守黑,有无相生。 可惜,瓶口有补过的裂口。本来这个瓶子会很贵,因为这个补疤,很便宜就卖给我。在家里放了十多年,总是耐看,只是那个疤,补得很可疑,没有点石成金。 最近认识了昆明的焗匠世家出生的付忠华师傅,请他帮我修补了这个花瓶。焗匠就是补锅匠,少时经常看见他们挑着担子在武成路周边的巷子里走,都是男的,扁担端上挂着个冒烟的小烽炉。他只要站在巷子口一吆喝,邻里就拿着各种破裂、通洞的家什,锅碗瓢盆、盆盆罐罐来补。补锅匠讨一碗水,用个土碗调碗鸡蛋清拌石灰粉,摆着,拉开风箱上火,烙铁在炉口烤着,一边用锉子、砂纸打磨裂口,之后在裂口上涂些镪水,烙铁一红,就在锡块上切割,嘶嘶冒烟,迅即变成银子般的液体,流到裂缝上去,漏洞裂纹就止住了,犹如一道闪电被固定。这是补金属器皿。 补锅手艺人雕塑瓷器是另一种补法,功夫更复杂更慢。裂片接起来,像是绣片。这些瓷碗太美,太顺嘴,就是裂了缺了也舍不得丢。要补起来。补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无论如何部,损坏的器皿就像是小的废墟,回不到原来的成品了。但是,焗匠将它创造成一个成品,超越它本具的正确。焗匠就像是在玩炼金术的浮士德,只是不在实验室,他蹲在地上。这种手艺是经验的结果,没有什么科学论证,也不会有人问是什么道理。各种的家什摆在地上浩浩荡荡排着队,补锅匠就像马戏团的魔术师,他一来,就顺便带来一个小型节日。婆婆、媳妇、娃娃、闲人(通常都是男人)二流子、乞丐、火枪(昆明方言,小偷),都站在旁边看着。妇人们唠叨些水井旁边听来的事,叽叽喳喳。 付忠华是位孤独的大师,少时就跟着家人学习这门手艺,如今在昆明城像他这样炉火纯青的焗匠寥若晨星,谁还愿意补,全新的才是好的。世界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他的手艺失去了谋生的能力,像诗一样无用。他继续做,只是因为爱好、喜欢,他成了焗艺术家而不再是补锅匠。焗是一种艺术,与写诗一样。他不能靠焗谋生,他经营茶叶、玉石,以这些供养他的焗事。付师傅四十几,相貌端正,皮肤白皙,话不多,有点诚惶诚恐,对生命深怀感恩之心的样子。带着四五个徒弟,铺子里挂着个大铜锅,下面升着泥炭火,经常煮着鸡、排骨之类。亲戚好汉茶客经常来他店上吃喝,有时候抹抹嘴走掉了,都不知道是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德的所指变了,仁还是仁,艺还是艺,艺失去了谋生的实用性,从小恩小惠里解放出来,皈依了大道。 宋代汝窑瓷片标本与现代汝瓷碎片在中国,高人都是手艺人。写诗要用手,写文章要用手,读书要用手。(孔子韦编三绝,就是用手。)画画要用手,写字要用手,木匠要用手,铁匠要用手,种地要用手,焗要用手。付师傅的焗非常有想象力,他甚至故意打碎新的茶杯再补起来,他不知道劳森伯。我把我的紫陶瓶子递给他,他系着围腰,戴着袖套,用个小锤子敲敲那个疤,一听声音就笑了,塑料补的。这个疤我一直看着不顺,质感可疑。原来是塑料片用胶沾上去再上色。这个疤揭下来,紫砂的本色就在裂口上露出来,土红色。付师傅的补法与原来的补者不同,原补只是想蒙混过关,赶紧卖掉,慌里慌张,所以补得拙劣,稍微细看就露陷,令人不爽,最后还是只能便宜出手。 付师傅的补法是实事求事,不是以假乱真,老老实实,用一块与紫砂风马牛不相及的材料去补它,不忌讳这就是一个补丁,光明正大的补丁。这种补法可以叫以诚补诚,他要补的是这个瓶子的圆满,厚重,不是这个瓶子的残缺,残缺是无法补的。他抱稳瓶子,在上面磨连接面,打孔,穿铜线,将锡块用电焊枪融化,补在欠缺处;打磨,抛光,等等,许多琐碎的手工。一个多小时,那个缺口已经补好,材料不同,厚薄、弧度顺应了它本来的线条。依然饱满,厚重。这是这个瓶子的第三条命:第一条命是戴得兴赋予它的;第二条命是那个将瓶子撞下一块的人,他没有令它粉身碎骨,只是少了一块,这是救了它;第三个命是付师傅给与它的。付师傅最后略施小计,将这个补丁做旧,补丁看上去像是戴得兴的原创,他就是这么上手的。 现在这个瓶子是三个人的作品:戴得兴,无名氏,付忠华。一场漫长的焊接,从民国初年到年,大概一世纪了,第一个作者已死,第二个作者不知所终,第三个作者补好了他,抱出来递给我,像是抱着一个婴孩。 我是第四个作者,将这个瓶子的故事用文字记下来。结绳记事。 我没有用它养花。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于坚,字之白。祖籍四川资阳,生于昆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写作至今,著作四十多种。系诗《尚义街六号》《〇档案》《飞行》《巨蹼》、散文集《挪动》《巴黎记》、摄影集《大象.岩石.档案》、纪录片《碧色车站》等之作者。本文原标题为“焊接”。燕京书评原创稿件,转载请后台联系。 点击关键词阅读更多文章 燕京访谈:冯尔康专访葛剑雄专访 赵鼎新谈民主自由 梁鸿谈梁庄 萧延中专访 《黑人民族主义声音武器》创作者专访 扶霞·邓洛普专访 贺欣谈离婚冷静期 程猛谈农家子弟 十年砍柴、张宏杰谈帝国官场燕京讲稿:陆扬谈现代历史学|张国刚谈中西文明|华兹华斯及其时代|金冲及谈做学问|阿乙对谈斯蒂纳·杰克逊|美国通识教育 燕京书评:霍夫施塔特的对与错|怎样阅读齐泽克|男孩女性化|保罗·索鲁在中国|美国记者推动社会变革|吉卜林的晚期风格|评阿甘本《散文的理念》|马凌评《记忆记忆》|冯洁音读《文化失忆》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suoe.com/llly/9027.html
- 上一篇文章: 每日推荐
- 下一篇文章: ldquo恶之平庸rdquo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