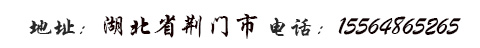许宏考古学是门残酷的学科,考古与车祸命案
|
采写丨张弘全文共字,阅读大约需要9分钟我们所谓的“夏”,应该是狭义史学范畴的概念,现在只能把它作为一种推论、假说或者可能性,它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是属于需要探索的问题。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代文化,但不能肯定。二里头遗址博物馆 在很长一段时间,考古学似乎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它高深莫测,与公众很遥远。考古学者的著述最主要的是考古报告,读者仅限于考古学同行和历史研究者。考古学者一头扎进考古工地,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与公众相往来。尽管每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有媒体报道,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颇有崖岸自高、孤芳自赏的姿态。包括岳南在内一些作家所写的考古发现类纪实著作,尽管也有一批读者瞩目,但专业的考古学者很少直接面向公众写作或交流。 作为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发掘队前队长(年-年),许宏改变了这一现象。在专业的考古报告之外,他以深厚的学术积累和长达二三十年的考古发掘经验,直接写作面对公众的普及型著作,此前出版的《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等著作都备受好评。此外,他还开通微博,长期与公众直接交流,迄今为止已经有多万粉丝,是不折不扣的大V。 近日,许宏的著作《发现与推理》面世。本书隐含着许宏作为一位资深考古人的学科反思:考古,需不需要有想象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运用想象力?假如没有想象力,很多考古发现便无从谈起;然而,过度解读甚至误读,又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考古学者该如何与无言的地下遗迹进行对话?这不仅依托于文物的发现,考古学者自身的专业敏感与推理能力也很重要。书中追述了几场重大考古事件的始末,不仅以亲历者的视角,呈现出考古现场的复杂性和魅力,也对几则著名的考古“悬案”重新展开考察,以专业者的慎思明辨澄清了其中的是是非非,提炼出极具启发性的学术思考。 就本书涉及到的问题,如二里头是不是夏代文化等问题,《燕京书评》专访了许宏。因文章较长,所以分两次发布。今天刊出的是第一篇,明天将刊出第二篇。 许宏,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从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 面向公众的著作有《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东亚青铜潮》等。 ▌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从阳春白雪到公众考古燕京书评:在你之前,很少有考古学者以专业为背景,写作一些普及型的考古研究性著作,你的《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引发了读者的很多好评,而这本《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也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我感觉,你写这类著作,潜在意味似乎是倡导一种理性、客观认识中华文明、认识中国历史的态度。你具体是怎么想的? 许宏:一些出版人说,现在跟考古相关的书有三大类。第一类是阳春白雪,像我主编的《二里头-》,五大本卖块钱,印上0套出头,全球范围内就不用再重印了。这种书跟公众没有关系,但它是考古人安身立命之本。第二种,就是把各种中国考古大发现攒起来的书。第三种介于二者之间,就是像我这样田野考古一线的考古人撰写的考古发现背后的故事,这类书虽然不多,但从社会效应来说,好像很看好,好多出版人都希望能出这样的书。 我自己认为,写这一类书是时代的产物。你之前也采访过考古学界一些老先生,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考古学处于一个剧烈的转型期,除了学科内部的若干变化外,那就是从象牙塔学问转向面对公众。这在我个人身上具有典型性。年,《读书》杂志主编汪晖组织李零、陈平原、葛兆光、陈星灿等人搞过一个笔谈,讨论“考古学与人文知识问题”。我们现在的所长陈星灿先生发表的那篇文章,题目就是《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我当时深以为是。他们几位学者共同提出了对以前考古学的不满,因为以前的考古学跟公众渐行渐远。 今年,正好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在百年前,考古学是作为一个显学出现的,因为它诞生于古史辨和西风东渐的氛围下,在故纸堆里已经没法进行文化溯源的工作了。而当时需要解答的大问题是: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中国是怎么来的?中国考古学,恰恰是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本来,考古学首先应该回答公众特别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uosuoe.com/llmj/8974.html
- 上一篇文章: 规划几个月,建成一两年,专治各种ldq
- 下一篇文章: 杜威与反亚裔仇恨百年前的种族歧视能给我们